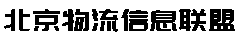01
将学术融入生命
任东来先生是我所见过的最有激情、最具天赋、最为敏锐的学者,他对一切新鲜的学术资讯都抱有浓厚的兴趣,能以极快的速度把握其核心内容,然后简明扼要地表达出来;其思想之活跃、思维之敏捷、思路之清晰,常常令我钦佩不已。他对学术问题,似乎有与生俱来的热情、领悟力与理解力,学术完全成为其生命的一部分。
孔子云:“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对于学术问题,任东来先生不仅是“好之者”,而且是典型的“乐之者”,是真正以学术为志业、以学术为乐的人。
他出身大学教师家庭,从小就显示出读书、写作的天赋,小学时作文常被当做范文在班上宣读;在宁波读中学期间,就办了当地图书馆的借书证,经常借阅课外书籍。1978年进入大学后,班上不少同学是“饱学之士”,或通古代文史,或懂近代学问,或精马列经典;他自谦是白丁一个,只好恶补苦读、埋头追赶。“大学高年级时,一套出自美国名记者威廉·曼切斯特的《光荣与梦想》,给我打开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原来一个国家可以如此多元而不至于解体,一个社会可以如此多样且可以繁荣发展,一个民族可以如此混杂却不至于四分五裂。由此,这样的感慨便引导我走上了美国研究的学术道路。”
此后,、杨生茂、冯承柏等老一辈先生的指点,他的学术视野日渐宽广、学术兴趣日趋浓厚,在史与国际关系理论两个领域,取得了不俗的研究成绩,也体会到了学术世界里的无限乐趣。2000年前后,,:影响美国的25个司法大案》、:、:,还自己动手、指导学生翻译了这个领域的一系列著作,、《风暴眼:、《反对有理:、《最民主的部门:。完成每一部著作,几乎都是一次愉快的学术之旅。
任东来先生很享受读书、写作带来的乐趣,在学术日益组织化、团队化的时代,他不属于任何研究基地、重点学科,也不是任何类型的杰出人才、学术带头人,甚至连培养对象都算不上。但他以一己之力,完全凭自己的兴趣,在史、国际关系理论、,都做出了有目共睹的贡献。这其中,也离不开他敏锐的学术洞察力。
任东来先生具有捕捉学术热点的超凡直觉与能力,他几次学术转型,都能占领甚至是引领学术前沿。研究生期间,他的学术训练集中于美国外交史与史,。工作以后,他的学术兴趣扩展到当代的、,写作了中美最惠国待遇问题由来、,后者被誉为国际关系研究中采用比较分析方法的范例。这些论文敏锐地捕捉到了1990年代中的热点,从历史与比较的角度澄清了当时知识界的一些误解。与此同时,他还率先将国际关系理论领域的“霸权稳定论”以及与之相应的国际制度理论,准确地介绍给国内学界,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提供了新视角。此外,他还在国内较早地介绍、。这些,无不体现了他敏锐的学术洞察力。
当然,任东来先生最精彩的学术转型当数从美国外交与国际关系,。大约在2000年前后,,并从此迷上了这一全新的学术天地。
2004年初,,大受学界欢迎,很快再版,并被制作成有声读物,广为传布。教授称,“本书最大的价值就在于,,向读者展示了一部形象的美国宪法史。这幅历史图画在细节的刻画上栩栩如生,而评论则从大处着眼,要言不烦,对于相关制度演进的过程及其历史和现实的意蕴给予了深刻的揭示。”
但是,,这一领域还只有留美的教授、王希教授等不多的几位开拓者,,远不如今天这般热切。但是,任东来先生已经意识到,这是一个极有学术潜力、乃至学术市场的领域,值得全心投入。时间证明,他的预感是对的。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众多媒体记者追思、缅怀先生的一个契因。
,任东来先生从未停止探索的脚步,司法审查、堕胎权等重大问题,都曾留下他的研究印迹。但最令人惊讶的还是他对持枪权问题的关注,,他立即意识到,美国宪法争议与“文化战争”出现新动向,随即与自己指导的学生就持枪权问题的宪法解释展开研究。2010年,,持枪权是一种不受各级政府侵犯的个人宪法权利,印证了他的直觉与学术眼光。实际上早在2002年,在讨论《武装美国》这部有争议的获奖著作时,他就察觉到,持枪权与堕胎权一样,是美国“文化战争”、。
在其厚重的学术人生中,除了浓厚的学术兴趣、敏锐的学术洞察力外,任东来先生还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
,、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他曾谈到,中国人讲宪法已近百年,却不知晓宪法的本义在于限制政府、约束官员和保护公民。在他看来,,,;美国的经验表明,,,而取决于制度、文化和人。因此,,关注的重点不是纸上的宪法条文,。”在李剑鸣教授看来,“任东来教授的现实关怀,。他经常以快速的反应、灵动的文笔和不俗的见解写作时评,发表在许多报纸和刊物上,让人领略了一个史家看待当前世界的方式。”
02
“功夫在诗外”
任东来先生口才出众,讲话节奏分明,抑扬顿挫,不时爽朗大笑,兴之所至,甚至会拍大腿。听他讲话,可以说是一种享受,作为弟子,我们都很乐意跟他聊天,但是必须给他提供新鲜信息,激起他的谈话欲望。
谈话,是他表达学术观点的重要形式,也是指导学生的一种方式。读书期间,只要他在国内,我几乎每周都有机会听他讲故事、发议论,有时是在课堂上,有时是在他办公室,有时候是在饭桌上。或是因为一篇文章、一本书,或是因为某个人、某件事,只要与美国历史相关,他都能信手拈来,谈上半小时。
他讲话极有条理,思路清晰、重点突出,绝不绕弯子,让人一听就懂。他的办公室永远向学生敞开着,没课的时候,他一般都在,我们如果想过去找他,事先打个电话说一声就行。不管是不是他自己指导的学生,只要是请教问题、或是与读书写作相关的事,他都乐意回答,愿意帮忙。
任东来先生讲课、写作,都有一定的故事性和趣味性,他也曾经跟我们讲,历史应该是一门有趣的学问,好的历史学家都是讲故事的高手,。他希望“熔学术著述的准确性和通俗读物的可读性于一体。既要有基本制度的介绍,又要有人物的活动;既要有宏观历史的观照,又要有具体的情节,甚至是悬念”。
为此,他和陈伟老师确定了三个写作原则:“第一,以案说法,法在案中;第二,以事说理,理在事中;第三,词章并茂,雅俗共赏。当然,这一切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的主题,那就是,从纸面上的宪法文本,,是一个漫长的进程。美国的法治建设,不仅仅有赖于那些法律精英:法官、律师、立法者和执法者,而且还离不开无数的芸芸众生、那些被压迫者、被歧视者、甚至是罪犯为自己宪法权利的苦苦追求。在一定程度上,一部美国的宪法史,正是这些勇敢的小人物不懈地争取自己权利和寻求社会正义的历史”。
,已经成为中国读者了解美国宪法的必读书籍。但是,任东来先生的故事还没讲完。他沿着案例之路,追根溯源,。作为后续姊妹篇,:,只不过更具有系统性,,,详略得当,要言不烦。
与他在史领域的研究成果相比,,并没有太高的学术深度。他自己也说,“我基本没有办法做出像史研究中那样原创性成果,我只能在国内的学术参照系中做得最好,同时尽可能争取更多的读者,让他们分享美国的法治经验。”于是,他放弃学术的深度,转而追求学术的广度与社会价值,结果大获成功,广受欢迎。
学术的深度与广度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要有深度,必须有一定广度。任东来先生多次用老农种树的故事来比喻两者之间的关系,这个故事是他从比较法学家沈宗灵老先生那里听来的。“先生告诉我,在乡下劳动时,他特别注意到老乡种树的经过。根据树的大小,农民先大概画一个圈,挖一个坑,然后,把树放进去试一试。不够深的话,继续往下挖,这时候往往会发现,原来的口子太小,深不下去;然后,再加大口子,这样才能够继续深入,几经反复,一个树坑才挖好,能够与要种的树完美契合。从农民的种树中,他悟出了做学问中‘博与约’的关系,没有一定的博,就不可能达到相当的约。这是一个不断自我意识、自我调整的过程”。
任东来先生自己就是一个知识广博、见闻丰富的人,他经常对我们讲,读书、写作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各方面的知识、理论都要涉猎;做学问,就像学作诗一样,“功夫在诗外”。他主张多选修其他专业课程、多听名师讲座。1986-1987年,他在南京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学习期间,、“国际关系”、“比较现代化”等新课程,而不是自己原本已经十分了解的和美国外交方面的课程。
在日后指导学生的过程中,他也一再鼓励自己的学生选修其他专业、甚至是其他学科的课程,多吸收、借鉴其他领域的研究成功与研究手段。就我个人而言,在硕士研究生阶段,除了修读任老师和历史系其他老师的课程外,还到法学院选修和旁听了几门课程,深刻感受到历史学与法学的不同视角和研究路径。针对同一个宪法条款,两者的思考方式截然不同:如果说历史学以线性推导为主,强调前因后果,法学则以平面扩散见长,注重理论层次。
任东来先生的本行和研究领域虽然集中于美国历史,但他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却在中国。他一直强调,学习外国历史,必须以中国历史为参照。他曾推荐我们阅读李剑鸣老师的文章《本土资源与外国史研究》,认为“这是一篇非常好的文章,告诉我们要成为一个优秀的外国史研究者,为什么要了解中国的历史”。
在他给学生所开列的书单里,有三本书中国历史方面的书是必读的:顾颉刚先生的《古史辨》(第一册)、。其中,《古史辨》对他的影响最大,顾先生在《古史辨·自序》中提出,学问“只当问真与不真,不当问用与不用。学问固然可以应用,但应用只是学问的自然结果,而不是着手做学问时的目的”。任东来先生因此坚定了自己作为学者的职业目标:“为学术而学术”!学问的“真”求出来了,自然会有人去“用”,但这“用”是别人的事,而不是学者的责任。
求真就必须从史实出发,不讲空话;必须沉下心来,甘愿坐冷板凳、坚守书斋,追求《桃花源记》中“武陵人”的境界:“缘溪行,忘路之远近”。我们都是学术河流里的渔人,但是能发现“桃花源”的人却是凤毛麟角。我想,在学术世界里,任东来先生也许找到了自己的“桃花源”。
03
爱写作也爱生活
任东来先生是一个待人真诚、热情、心无城府的人,从来不愿以恶意揣测别人。他对学生,批评时严厉,指导、帮助时却竭尽全力、毫无保留。学生的每一封邮件,他都会及时回复;学生给他的每一篇文章,他都会逐句修改,提出具体建议,反复多次,直到他认为合适,才会推荐发表。
刚进师门时,我的第一篇习作,被他修改了不下五遍。后来在他指导下翻译英文著作时,他也是仔细对照,每行必改。他常常对我们讲,文章不厌千遍改,好文章都是改出来的;修改文章是学术训练的一个重要环节,与上课、读书同等重要。对于实在是改不下去、自己又不满意的文章,可以先放一放,以后发现新材料、有了新想法,再补充完善。
他对自己的文章也是如此,1984年读硕士时,他曾写一篇关于美国历史上联邦法令废止权问题的习作,一直搁在书橱里,直到2001年才修改发表,距离该文最初完成时间整整17年!
2002年前后,任东来先生开始在报纸上开设国际评论专栏,以生动的笔调、敏锐的眼光、独特的视角,介绍、分析世界时事的历史背景与文化意义。他将写评论视为学者服务社会的一种形式。他也希望我们勤写作、多练笔,“对书本的知识和现实的世界永远保持探索的欲望,随时把自己的想法和看法记下来,持之以恒,一定会有收获。不论你们以后做什么,观察和写作能力永远是有用的”。
任东来先生非常强调书评的作用和价值,他常说,学者的本职工作就是读书,书读多了必有感想,把感想记下了,就是书评。但是写好书评并不容易,必须有学术史上的整体把握,必须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指明不足;惟其如此,方能裨益学界,推动学术进步。他不但指导学生写书评,自己更是身体力行,写作了大量颇有学术分量的书评,其中不乏有情有理的佳作,比如,他为《战后世界历史长编》所写的“墓志铭”——《纪念一项延续了四分之一世纪的学术事业》。
任东来先生学术视野宽广,学术交流广泛,多次担任国内美国史专业毕业生的论文评阅人或答辩委员,提出了不少中肯的修改意见。他还作为一些重要杂志的匿名评审人,评阅青年学者的论文,提供修改意见,指导、鼓励他们完善研究。在这些学生和后辈面前,他没有一点架子。无论是谁,只要是跟他讨论学术问题,他都会热情回应,甚至掩饰不住兴奋之情。他是少有的对学术问题充满激情、永远好奇的学者。
也许正是因为他的这种激情、这份好奇心,使他一直朝气蓬勃。在我的印象中,他似乎永远是个充满活力的年轻人,与我们之间并无时代隔阂。他几乎是学校最早使用电脑写作的历史学教授,也几乎是最习惯于用电子邮件跟学生联络的历史学教授。从他那儿,我不仅学到了写作、修改文章的方法,甚至学到了使用Word的一些技巧,比如修订文档、制作目录和索引等。修改学生的论文、译作,需要占用大量的休息时间,但他从不抱怨,也不马虎,有时候甚至会跟我们调侃一番。
在生活上,任东来先生也是个乐观开朗、极易相处的人,对新鲜事物同样充满好奇,并且乐于跟别人分享自己的快乐。记得2004年刚买车时,他开车带学生去郊游、野餐,在邮件中通知我们,“专车运送(附赠人身保险),要带‘特殊’朋友,请赶快报名,除了准备好心情和好胃口外,不需要带任何东西。”读书期间,只要有新生入学或是毕业生答辩,他必定请全体学生吃饭,学校附近的中西餐厅,几乎都留下了我们的欢声笑语。
任东来先生常对我们说,学美国史有个好处,能长寿。对此,我深信不疑,因为他的话太有根据了,美国史研究领域的几位老前辈,均得享高寿。1913年出生的刘绪贻先生、1915年出生的黄绍湘先生,已是百岁老人,至今康健;,杨生茂先生去世时93岁(1917年生),1920年代出生的曹德谦、邓蜀生先生也已年届九旬。任东来先生跟上面的每一位老先生,几乎都有私交,从那些充满温情的回忆文章可以看出,他是一个重师恩、念旧情的人。我知道,数十年后的某一天,我也会写下回忆恩师的文字。但我实在没有想到,这一天竟然如此之快,让我猝不及防、来不及反应,不敢回忆,也不愿回忆。本以为“百年己分,可长共相保”,谁知一年之内,阴阳相隔,永不得见,岂不痛哉!
![]()
任东来、白雪峰、陈伟 著
中国法制出版社2015年
本书并没有就法律谈法律,而是用生动的笔触,翔实的资料,描述了法治在美国社会的各个方面从生根到开花的历程。,是一以贯之而又不断发展的一种观念,一种精神。,让读者去细细回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