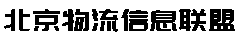
2022-03-05 12:46:23
张杰诗歌研讨会
时间:2017年5月27日(周六)下午15:00-18:30
地点: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二楼会议室
主持人:王东东博士
说明
以下发言稿,根据各发言人现场录音与文稿整理,按发言先后顺序排列,因时间所限,一些到场发言人拟定好的发言稿未及讲完的,也依据文稿进行了完整录入。部分未到场诗人为研讨会准备的发言稿,也一并收录。本此研讨会发言稿经主办方授权发表。
此次研讨发言诗人、评论家有王东东、陈庆、张备、苏丰雷、桫椤、陈家坪、罗羽、南桥琴、欧阳关雪、高爽、陈志伟、宋琳、周伟驰、李建春、张依苹、杜涯、小庄、北渡、徐帅领、史大观、张杰,因微信公号字数所限,下面综合选取了诗人王东东、宋琳、杜涯的研讨发言。
王东东:
诗人、评论家,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华语诗歌研究中心主任
输12
前一段张杰兄说在平顶山办一个范雨素现象的讨论,大家知道现在有个底层作者范雨素,可能我们同学也关注了。然后呢,我们也计划把这个活动放在张杰兄的故乡平顶山市,后来因为其他的原因,最终仍确定在新乡举行。当时我为什么和张杰兄做这个张杰诗歌的朗诵会和研讨会,大家知道,我们这个(河南师大)华语诗歌研究中心,在做一个小型的“中国70后诗人见面会”,第一次做得是70后诗人陈家坪,因为我对张杰兄的了解,是始于十几年前,那时我到北京考博时,臧棣赠给了我一套“千高原诗丛”,有十本诗集,是张杰兄责编的,其中有一本是张杰兄的诗集(《琴房》)。
当时我对张杰诗歌的印象很深,可以说他是中国70后诗人当中的一员大将,所以说我认为应该纳入到我们70后诗人的研讨当中来,包括最近几年,我也关注他的新作,我觉得他的写作,已经有个人的鲜明的风格,尤其是摆脱了中国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叙事性的影响,而逐渐的具备了一种智慧抒情,或者说,一种智性抒情的品质,这点也和我对中国当代诗歌的观察相一致,所以我对张杰诗歌是抱着一种极为钦佩的态度。
那么,尤其谈到他最近的诗作时,我们觉得他的诗可以说慢慢的具有了一种风骨,觉得可以用到这个古典的批评观念,用刘勰(《文心雕龙•风骨》)的话说就是“风清骨峻”“蔚彼风力,严此骨鲠”,“蔚彼风力”就是(文章强盛有力)蔚然成风的意思,“严此骨鲠”就是(语言文辞)它的内在架构必须要是致密的,这样它在飞翔时,它才不会破碎,如果我们把(文章)它比喻成一只鸟飞翔的话。
刘勰在《文心雕龙•风骨》也用到了一个比喻,就是一只鸟飞翔,就是什么样的鸟才能飞翔,就是它要有风,它还要有骨。我觉得尤其是张杰兄最近的诗作,可以说,达到了一种愈来愈精纯的状态,比如说他会有意地通过造句,炼词造句,留下让我们印象比较深的诗句,我个人认为,如果说一两百年之后,我们这些当代诗人,如果被人记住,可能也就是被人记住几行诗,几首诗,所以我对他这种炼字造词,其实我个人还是蛮欣赏的,所以说我因为有对张杰兄的印象,对他诗的了解,所以我当时就建议说要做张杰诗歌的研讨会……
(张杰)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的诗人形象,在我们的当代有一种理想主义的荒谬甚至荒诞状态,但这与其说是张杰的问题不如说是我们时代的问题。另外,新世纪以来的诗歌与90年代诗歌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的位移,这可能跟个体的感受有关,也跟个人的写作有关,对历史的处理,还需要进一步塑造,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做70后的这样一个批评的原因,因为我们参与塑造着当代诗歌的最新面貌。……这是一个难得一见的诗歌讨论的瞬间。在某些人的个人记忆里,还是有裨益的,想到这一点,这在我们这个时代也是不容易的。……我们对张杰、渐成气象的七零后诗人、甚至新世纪诗歌都认识和肯定不足,而这本应是我们批评的目标。
宋琳:
诗人、画家
输12
我与诗人张杰相识已有十二年了,第一次见面是在新疆的“帕米尔诗歌之旅”途中,那时我还未读过他的诗。之后在北京,我们时相过从,便渐渐熟悉起来。他质朴,神经质,书生气,为人热情又敏感于伤害,对京城的环境和诗歌圈似乎格格不入。他编辑民刊《爆炸》向我约稿,又将我的诗发布在《诗生活》网站的诗人专栏里,还对我做了访谈,这样我就有机会读到他的诗,并了解他的诗学倾向。2008年,由他责编的千高原诗丛在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他送了一套给我,其中有他本人的诗集《琴房》——内敛,安静,蕴含着爆破力,形式相当稳定。我的推荐语保留了当年读这本诗集的印象:
张杰的诗歌有一种朴素的温情,它不依赖公共语境中的词语而发声,而是在心灵与万象的冥会中,逐渐发现一条“用沉默沟通”的言说之路。
一个诗人的言说之路首先取决于他的语言态度,正是在语言问题上使得同代人之间或殊途而同归,或同途而殊归。瓦雷里观念中的“克难”就其在语言运作层面上如何将言说难度设置为通往诗艺高峰的移动坐标,在任何时候都是有效的,公共语境中的词语是单向度的、在日常交流中被损耗甚至用罄的词语,诗人的言说应该与公共语境保持审慎的距离,就是说,自觉地做一个语言的少数派,因为表面上容易达成的交流往往不具有内在对话性,对于确立了个人诗学理想的诗人而言,美学的偏执是必要的。
此即鲁迅所谓“不和众嚣,独具我见”之孤独个人者。这并不意味着书写必然属于不及物的行为,恰恰相反,形式主义者忽略了命名的伟大意义,凭借命名,物获得了词性,而未获名称之物乃是一种沉沦,从此意义上说,诗性的言说不仅是及物的,而且是对无名者的招魂。名者,命也(《说文解字》)。汉语字源学为我们提供的诗学出发点,同时确保了诗人的天职是将事物从无名中拯救出来,使它们免于沉沦。无疑,这种将事物带入存在的难度不仅是言说之难,亦是致良知之难。
我近日读到张杰的《我的新诗写作浅谈》,他在文中强调了叙事诗学对当代写作的重要性,当然是对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叙事方式介入写作的某种共识的呼应,从他的早期诗《弃儿》中,我发现他的实践与一度流行的“伪叙事”观念判然有别。这首诗取材于“1983年的‘严打’和一个底层小人物张文艺的悲剧命运”,这位与作者一道长大的“儿时大院青年”,因赌博输钱,与人合伙“夜洗了露宿街檐的菜农”,劫得二十元而获刑十五年,保外就医后死于车祸。诗的第九节记录了作者与诗中人物的最后一次分手:
在邓丽君甜柔的歌喉里,我们在车厢似的
黑巷里分手。蓦然,他说他是一块
活着的石头。摆摆手,我们便各自在歌曲里
漂走……走出巷口,我的心被抽紧、
加速,有谁知道呵——时代大杂院里
那块活着的石头——啊石头
情感的强度是通过重复而递增的,“有谁知道啊”多么有力地道出了被抛者的无保护性,而那块自我指称的石头亦置换成了作者的心石,它是有棱角的,犹如墓碑。而当我们在另一首诗中读到“关于这些,我不说谁又会知道”(《记一个下雨的冬夜》)则仿佛听见了某种回响。见证乃是说出,乃是听见沉默并用声音中的沉默沟通无声的沉默。
诗人被赋予说的权力,唯因诗人的天赋是能说,且这种权力是不可让渡的。《弃儿》为小人物张文艺立传,亦是为他的悲剧命运代言,没有这首诗的存在,这个时代的弃儿将永远湮没无闻。荷尔德林曾写道:“但难的是/在伟大之物中保持伟大之物”(《帕德摩斯》残篇),而在当下中国,或许将渺小之物从遗忘中召唤出来,正如将弃儿领回存在之家,让卑微的命运通过诗歌开口说话,才是某个正当的开端,因为只有寓于渺小之物之中才能开启伟大之物,诗只有同时见证二者才能不重蹈高蹈派的覆辙,这里,之所以另辟蹊径的隐微叙事使得宏大叙事失效,秘密就在于“心声也,内曜也①,不可见也”(鲁迅)。
一个诗人关心社会底层的艰辛与不幸是天经地义的,儒家诗学所谓“发乎情,止乎礼义”早已形成传统。《毛诗序》曰:“发乎情,民之性也”;朱熹评价屈原:“盖屈子者,穷而呼天,疾痛而呼父母之词也。故今之所欲取而使继之者,必其出于幽忧穷蹙怨慕凄凉之意,乃为得其余韵。”②而时下的“底层写作”之论实非什么新发明,《击壤歌》、《国风》岂非劳人思妇之所作?以身份论诗并依此判别诗之优劣根本上放弃了诗的标准。另外,关于地方性知识的重要性,在谈《女神》时也已说得很清楚,地方色彩须与时代精神相对应来思考,否则缺乏现代性的乡土诗之泛滥就得不到鉴别,诗艺上“更高的运作”则被遮蔽因而晦暗不明。
不记得哪位美国诗人曾说:诗人若不处理脚下的土地,他就没什么可写。这话本包含在介入诗学的要义之中,固然如此,但诗人所要处理的现实并不宥限于乡土,题材无高下,关键在于“诗之灵的演进方式”(荷尔德林)。与一些被追捧的底层诗人相比(其原因或少不了乡愿),我更欣赏张杰的独立不惧,处世不惊,不把自己生长于斯的平顶山煤城的日常生活当作盛事来抒写,他像矿工一样只知道更深地掘进黑暗,难道非得身为矿工才能写矿工生活吗?《雪,煤城》、《70年代:煤城旧事》、《挖煤工》、《命定的豫西小煤城》、,《恐怖小城》、《山西煤块》……如此多的煤炭源源不断地流出地面,仿佛地下黑河,却是他灵感的源泉,为他的诗提供能量,照亮他的精神:
所有面孔被煤里的千分尺冷漠度量
长成千人一面的无声煤矽肺、煤少女、煤老头
整个小城的眼睛还要在地下发黑三百年
煤才能被挖完
(《恐怖小城》)
这里,在威胁生命的,无保护的,严重污染的劳作现场,人业已异化为非人,个体业已失去特征,一代代老去,重复着相同的命运,看不到尽头。“整个小城的眼睛还要在地下发黑三百年”,人的境况如此严峻以致类同于活埋。而地上的情况又如何呢?“炼焦车间,煤仓皮带,大罐烟囱,正呼出沉沉白气。”(《国企,焦化厂,2013》)“寒酸的小酒馆,油布门帘里/裹满了醉意,在矿区/它永远和煤纠缠不清。”(《命定的豫西小煤城》)。
前文提到的诗人的“更高的运作”,意指“物物而不物于物”(庄子),在内化的灵视作用下,物我已然合一,自他无隔于毫端。艾略特称“将要充当那种特定情感表达式的一组事物,一种情感或一串事件”③为客观对应物,问题在于那些周遭的事物若无“幽忧穷蹙怨慕凄凉之”主体的迫切情感反应,则不能成其为对应物,所以我相信诗迫而成。王国维区别“观我”与“观物”,谓“二者常互相错综”,读张杰的诗,不能不欣赏他的“观物之微”,盖因他明白“非物无以见我”④的道理,这与凡诗必自我指涉,将傲慢之我挡在文本之前的写作相去何其遥远。
如果我们以为张杰只是一位地方性诗人,那就误读了他。无论北京时期或两年流寓海外时期他都有作品叙其行踪,大抵遵循古人“登山必赋”的信条,他也多有山水之作。例如,2005年南疆之行,他写成《新疆作》,视野不可谓不空阔,近期以“游仙诗”冠名的诗作也颇具“自然之眼”。总体上,他的气质偏于沉郁,生僻,偶尔晦涩。顾随说:“晦,可医浅薄;涩,可医油滑。”⑤虽然张杰有些诗在过渡时难免有语气不畅,而油滑则断然不见于篇什。《干面胡同》、《尘封的“夹边沟事件”》等诗对现实层面作考古式勘探,以期将历史记忆及自由之渴望隐微地折射出来。他近日的一篇长文里提出“忧郁机制下的精英意志和亚意识形态”写作,将公共语境中的诗人心境与意识相态反制置于新世纪诗歌发展的整体背景下进行脉络梳理,而他个人的诗歌理想可从他的一句诗透出机趣——“向尘世的自由星系致意”。
张杰的近期诗往往多用奇句险语,且不乏自造词。试举例如下:
直到它蓦然打开自我的羽旗(《对中原灰杜鹃鸟的描摹》)
鸟道士,身子在枯草里摆动(同上)
女眼,传动粉色温柔(同上)
出尘的蜗牛绿(同上)
白雾撞击、覆盖我们时,踩着温柔的脚刹(《冬的白雾》)
巨石宽窄成塌,令人放弃飞翔(《游鲁山李子峪》)
深山的阔大墓室,默默发出叹息(同上)
这些意象的营造颇得禅宗点铁成金之妙。韩愈所谓“险语破鬼胆”,为李贺、卢仝所效仿,目的在于出人意表,即“厌陈旧而欲新好”(陈师道)。沃洛希诺夫评价福斯勒“个体的创造性言语行为”和玛尔的“语言杂交”时提出了“陌生词语的哲学素(philosopheme)”这一概念:“如果没有陌生、神秘的词语,没有任何外来词语进入该民族的视域,那么,该民族就不可能创造出任何类似这些哲学素的东西。”⑥诗中的奇句险语因其陌生化而作用于读者的感官与心智,其功能不亚于“别求新声”的外来词语(包括古语再造)对母语演进的催化。诗的深度与抽象有赖于哲学素。方以智论诗曰:“不可以庄语,故以奇语写之”⑦而诗人欲挣脱平庸的公共语境与险恶的时代压力,首先需要“治其心”(方回),并如品达在《匹索竞技凯歌》中所唱:“在无谎的铁砧上锻舌!”
_______
①“内曜者,破黕暗者也;心声者,离伪诈者也。”见《鲁迅全集》卷八,23页。
② 朱熹:《楚辞后语目录序》。
③ 艾略特:《哈姆雷特》。
④ 王国维:《人间词乙稿•叙》。
⑤ 顾随:《李贺三题》。
⑥ 沃洛希诺夫:《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
⑦ 方以智:《通雅诗论》。
杜涯:
诗人
输12
我发言的题目是《由“骨秀”而迈向“神秀”的写作》:
一、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画像
在当代的中国诗坛,无论从各方面来讲,张杰都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诗人。
他的优点很明显:他异常地单纯、善良、率真、厚道,毫无城府,毫不圆滑、世故。他是透明的,如果说有的人心似海底、深不可测的话,张杰则刚好相反,他的心是一个小浅坑,里面只有一汪清水,一眼就可以看到底。他待人温和,像一匹马一样单纯,也像一匹马一样善良。而同时,他又性情耿直,满腔正义,疾恶如仇,遇到不平的人和事,常常拍案而起,甚至敢摸老虎屁股。他敏感、脆弱,容易受伤害,但“自愈”的能力也很强,很快便会忘记一切,心中也从不留怨恨。他多半时候都是阳光的,相信一切,几乎没有防人之心,随处播撒着他的热情和热忱,对朋友毫无保留地真诚,对陌生人也热心相待。
在火车上,他很快就会和周围的陌生人诚恳地交谈,给遇到难题的人出主意,开导悲观者;他鼓励一个准备到北京报考电影学院、但因怯懦而想退缩的女孩,称她是“整个火车上最有理想的人”;他曾向在火车上偶遇的一个有冤情而无助的湖南打工民妇伸出援助之手,在北京为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并为其振臂而呼……他生于底层,长于底层,对底层民众之苦深有体会,他对底层的那些无助无望者怀着深深的悲悯之心,甚至会为他们流下毫不做作和虚假的泪水。他是个行动者,许多时候不只停留在言语上,而是要付诸行动。他身上有一种勇气,也敢于担当。他喜欢做事情,也一直在做事情。
但张杰的缺点也同样醒目。他性格比较偏执、冲动,有时缺乏理性。他是个行动者,一般人若有某种想法或念头,考虑到条件不成熟或结果难料时,便会放弃想法或念头。但张杰则不,当他产生某种强烈的想法或念头时,便会付诸行动,他会去做,几乎不计后果:办刊物、去北京、出国……等等。
他的外表文质彬彬,然而他的内心却意志力强大,我们在北京在一起时,他总是强迫我去做我不愿做的事情:强迫我在网上露面、跟帖、发言,强迫我应邀去《诗刊》做编辑(出于生存和生活的考虑),强迫我开博客,强迫我与外界交流、交往等等。我的反抗是无效的,除非我想玉石俱焚,否则只有按照他说的去做,因为他偏执且意志力强大。然而,也正是他的偏执和意志力,他才在条件和环境都缺乏时,做到了别人在同等情况下做不到的事情:他办了诗歌民刊《爆炸》;他闯荡北京,在几个出版社做编辑,策划、编辑了许多图书;他去到马来西亚(为了心中所向往的“远方的自由、生活”),在学校教课,在赤道的灼热气浪中生活了两年……
张杰对诗歌有一种超乎寻常的激情,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对他来说,诗歌就是生活,生活也必须是“诗歌的生活”。如今,他又办了诗歌民刊《静电》,并和朋友一同创办、编辑了《将来之花园》诗刊,继续着他的蓬勃昂扬的诗歌理想……
二、“平顶山时期”和“北京、吉隆坡时期”
我和张杰是于2002年7月认识的,我在那时初次读到了他的诗歌。在我看来,张杰的诗歌可分为三个时期。他早期(2000年至2003年的“平顶山时期”)的诗歌很贴近现实,语言冷静,诗风纯正,题材也以煤城的风物、人物为主。他那时提倡“人性”,逢人便畅谈“人性”,也在诗歌中将其体现。他倾注着对人的苦难、命运和卑微之物的关注、悲悯,和自觉的责任承当,几乎与之同呼吸,共哀痛。这个时期他写了一些很优秀的诗歌,如《记一个下雨的冬夜》《命定的豫西小煤城》《琴房》《午夜湛河》《天井》《土山》 《万物正与墨色的我们匆匆别离》(组诗七首)《平顶山的雪》《那遥远的煤城......》等等。
这个时期,他在用词造句上已自成一家,但语言还是明朗的,是明白易懂的,仍属于一种普通诗歌语言。合乎规矩,毫不古怪,慰贴人心,既纯正,又正统。
2003年7月,张杰去了北京,在北京工作、生活了6年;2009年6月他又去了吉隆坡,在那里生活了近两年,直到2011年3月回国。这8年时间,可称为“北京、吉隆坡时期”。
(顺便说一下,我和张杰是2002年7月相识,2004年2月建立恋爱关系并在北京生活在了一起,没有结婚,2007年9月我们分手。我和张杰在北京在一起时,我不过问他的写作,也绝不允许他干涉我的写作。在个人的诗歌写作上,我远比他要固执。所以那时我们的诗歌写作互不影响。)
到北京后,一个广阔的世界呈现在张杰面前,北京丰厚的历史、人文氛围也激荡着他,同时,他也看到了更为丰富、复杂的人群、生活,。生活和环境的改变必然带来诗歌的改变。他开始关注、探察更为广阔、丰富、复杂的生活,并力图在诗歌中将其诗性呈现,发现其真知。“我们必须关注生活,里面埋伏着宇宙般博大的诗意可能。我们需要对现实生活的精微、复杂,做辩证的诗歌介入,呈现一种当代中国的诗意化真相。”(张杰语)
这个时期,他的诗歌开始缓慢但却稳步地上升,从具体、日常上升到了一个更高的精神层面。在诗歌中他开始自觉地减少了抒情,而增加了思辨、思想的成分,同时又不动声色地融入他的时代思考、历史意识、精神关注等,境界更加开阔,思想更加成熟:
干面胡同,深冬的灰脸模特,
被强化的灰,使bobo族颓废。
那些砖墙、石门墩,仍行走于
民国,瓦房,残破为古戏道具。
——退移灰色的钴蓝傍晚,
从北京娃娃眼涡里空茫颠簸。
干面,暗示出富足、温良,
似乎豪宅,刚被新面瓢舀出
雪白的新精神,客串着暮年
雪剧,屋顶,鸦声里沉郁——
寅时,小巷将灌满夜粉,沉睡
的铁条和颜料,突然间喧响。
而格窗,晃着榆树的枯枝骑兵,
它们的硬胡茬,雄壮而迷人——
——《干面胡同》2005.12
可以看出,这时他的诗歌语言开始有了变化,因所处环境的特殊性,他必须对一些东西有所避讳,于是,他的诗歌中开始出现较多的隐喻、暗语、象征等。而生活的广阔、丰富、复杂也要求他必须使用更高的语言。他自觉地突出到普通诗歌语言之上,突破规矩和正统,用词造句开始与众不同,打磨并且讲究,由实到虚,或由虚到虚。这样的语言读起来新颖、别致,甚有深味。
他把“写作定位在描述我们的生存处境和心理处境的实质,关注语言在具体语境与外部世界的关联,在诗歌中强调对事与物的准确性把握,追寻想象力的大胆创新和生发,不用僵硬土壤板结的语言表达,追寻语言的灵动,最终刻画出内部世界的丰富和对良知、人性、自由、民主和公民责任感等的承担,不是对物的关注,而是对精神的关注,从写作角度看这是更具有难度的写作,这一工作使得语言更广泛地被提升出诗意的可能。”(张杰语)
三、“蝶化时期”
2011年3月,张杰从马来西亚回到国内,经历了两年多生活的动荡、无着落后,于2013年冬天回到了平顶山他原单位的学校,生活终于重新安定了下来。我自和张杰分手后,对他的诗歌少有阅读,了解不多。因为要写这篇文章,读了他近几年的诗歌,有点吃惊,我发现,自2014年起,他的诗风开始出现了较大的变化,以至到今天,他的诗歌已经完全与众不同,焕然一新。自2014年至今的这个时期,我将其称为张杰的“蝶化时期”:他已从一只普通的蛹,化生为了一只光彩的蝶。我把他的这段时期独立出来,作为重点来讲。
2015年2月,当我初次读到黄灿然兄的《发现集》中的部分诗歌后,曾激动地在信中对他说:他以前的《奇迹集》是蛹,而此后的《发现集》是蝶,是一个新生的创作的开始。前几天当我读着张杰近3年来的诗歌时,忽然发现:这个“由蛹化蝶”的说法同样也很适合张杰,他近3年来的诗歌表明,他确已从一只蛹,化生为了一只蝶。
我把我这个“发现”在电话中告诉了张杰,并问询他:怎么会想到要用这样的语言写作?他告诉我:2013年下半年时,他因对自己的诗歌写作不满,便开始对自己的诗歌语言进行大胆的创新和创生,试图将现实、生活等用一种新颖的、付托于想象的语言呈现出来,以突出于普通的诗歌语言之上。经过他执著的探索、努力,于是便有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些诗作。
2014年春天,是张杰诗歌真正幻化的开始,他几乎通篇都构筑、使用奇幻的词语、变动转换的语言,手法几乎了无痕迹:
鸟道士,身子在枯草里摆动
寂静之门,它的变形
用拢翅的还乡步,搜啄着乱草
草籽,已备好新草丛的萌发,
风的通透臂膀,晃响林冠。
——《对中原灰杜鹃鸟的描摹》2014.3
幼年的白杨,延伸自身硕大的银针。
一个个建设的影子流飞进乳化的风中,
都似春天的战舰,在下午的舷窗外旋转
——《甲午之春》2014.3
褐雀从梧桐树丛,弹出一根虚线的舞蹈。
猫在梅花树下吃饭,滑动,震动空的波形,
偶尔,猫舌咂摸盆沿的时间线。
逸世的枝条,在深渊燃烧。
为晨明欢呼的鸟,为自我的清晨放音。
——《四月雨后》2014
他构筑新词,一些词语则被他重建,这些他构筑、重建的词语突破了常规,奇炫、奇峻而又变幻,刷新了读者的固有认识,使人耳目一新。
接下来,这种词语的构筑和重建已被他越来越多地运用,手法也越来越纯熟,时有闪光之语句出现:“橡皮清晨,在艰涩涂抹天空”,“栀子的绿像,闪烁在雨中”,“蒺藜刺破了手的问候,/野灌木尖锐,直率”,“植物天线,听到了鱼的气泡语”,“路边的白蒿,在落日电流中颤抖”,“麦的海波,在阳光机翼下/徐徐颤动,花粉的信号正醒来”,等等。
他的强大的意志力此时起到了关键作用,经过他执著而持久的探索,经过他坚持不懈的努力,到2016年、2017年时,他的写作已到达了一个全新的维度,他的诗歌已获得了一个全新的生命:他终于从一只普通的蛹,化生为了一只光彩的蝶。
一个注视进入雨的玻璃。
雨有雨的气宇。
石榴树低下头,身下积满雨洼,
雨纹,快速播映天空的扭曲。
渡雨的黑鸦,谈着寻到的新居,
两位冒雨赶路的旅行家。
……
饱饮的植物酣然而立——
醉意的自治,忽有飘花。
—— 《当代世界的雨》2016.6
月,沉没在铁壁星球最边缘。
金黄的地狱中,土地静如死海。
月儿也会登上我们内心的天梯,
指着众人应有的天堂。
不要以为月光不是自由的波涛,
月,也在运行自由意志的坟蒿。
不要以为月不是暴阳的威吓,
月,始终背着为我们受难的火鏊。
——《中秋》(一)2016.9.19
南方需要一种反向列车呼啸扑面而来的美。
绿狼般探索的怪兽,不停率领南方野性的出没,
野性的芦苇不在南方河边,而站在矮山上。
南方荒山呼唤着外星人发光的开拓与降落。
……
积木的城堡,拿出南方的阳光擦拭着钢轨。
什么是南方不可获得的?不能到达的?
南方的电线杆卧铺一样睡着——
就让南方的铁丝网扭动光的波形——
南方的空调一旦停下,闷热的思想将煨出蒸笼。
白苇静烧的火焰,静望着北方严冬,突然,
就饮下了南方春城,突然,云南就布下了云的蓝阵。
而大理的王冠,白云影,正王冠样戴在苍山山顶。
——《与欧阳关雪丙申冬末赴云南述怀》2017.2.16
在这些诗歌中,他技巧纯熟地驾驭着奇炫、奇峻而变幻的词语、变动转换的、时而朴拙时而灵动的语言,穿行在事物之中,遨游在天地之间,来去自如,收放自然,同时将他对时代、生活、世界的体察、发现、认知、思想等,或明或暗地融于诗歌之中,浑然无痕,悠游无碍,几乎达到了一种理想的自由、写作,获取了理想的文本。
自2014年春至2017年春,张杰写了近百首这样的诗歌。这些诗歌透着比较一致的风格:词语奇炫、奇峻而变幻,语言深雅、奇秀、清润、炫美,想象丰富而奇特,修辞雕饰而讲究,而诗歌的内在却整体又透出一种刚硬或刚健,隐含一种精神的力量。可谓“外秀而内骨”。
对此,张杰有他自己比较成熟的思考、努力方向:“时代某种意义即是苦厄,只有爱和醒悟的力量是甜蜜,我要尽可能地写出来,呈现一个批判和期许出来,而不能回避掉一种批判式的发言,我要朝着一种秀骨和神秀写去。在语言处理上,既决然又要与古风内通地传接,要寻求新的呈现,突破已有的种种平庸框定和思想禁锢,要呈现一种有音乐性的,精神与语言的典雅均衡和境界的上端,同时不失一种内在的真相思考和对未来新世界的期盼。”也就是说,“外秀而内骨”是他自觉的、有意识的追求。
“秀骨和神秀”的提法来自王国维,其在《人间词话》之十四写道:“温飞卿之词,句秀也。韦端己之词,骨秀也。李重光之词,神秀也。”
事实上,直到2016年下半年,张杰重读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时,才注意到他的“句秀、骨秀、神秀”之论说。张杰深以为然,并且他发现,自己几年来在诗歌上的探索、努力、写作,竟无意间与王国维的论说不谋而合。他明白自己此时的写作已达到了王国维所说的“骨秀”之境,便砥砺自己,自觉地开始向“神秀”之境迈进。
按王国维的审美评判标准,张杰的诗歌确实已具备了“骨秀”的品质,并已开始向着“神秀”的高度迈进。(其实,他的部分诗歌已具有了“神秀”的气韵和品质。)相比于“外秀而内骨”的“骨秀”,“神秀”应是一种更高的境界,闪耀着精神的光芒、力量,视界广渺,格调宏阔,气象高远,是一个诗人在诗艺、修为、学养、境界、思想等达到足够的高度后,在其诗歌作品中的自然而然的体现,是一个人的内在达于外在的自然的呈现。所谓“玉在山而草木润,渊生珠而崖不枯”。
具体到诗歌,则是由诗歌的语言、气韵、形式、技巧、内在的思想、以及诗歌的格调、气象等综合体现出来的。相信以张杰的对语言的天然的敏感、悟性,自觉的追寻、创新,执著而坚持不懈的探索、努力,加之其在学养、修为上对自己的严求、砥砺,最终他会达到自己所期许、所向往的“神秀”的境界和高度的。
四、当代“李贺”
我曾在少年时期读过李贺的一些诗歌。2008年3月至5月,我忽然深深迷恋上了李贺的诗歌,为他诗歌的奇崛、超拔、陡峭、为他语言的奇奥、生僻、璀璨而沉醉痴迷。那几个月里,我读了几乎所有李贺的诗歌,并写了一些奇崛、峭拔的诗歌,在词语和语言上求奇出新,并自造了许多词语。
后来,我总算从那种痴迷里出来了。那几个月的阅读和写作带给我的益处是:我学会了自造词语,在语言上也解除了桎梏,获得了自由。顺便说一下,我感觉现代汉语的词语是不够用的,有时某种感觉、意境、认识、思维等找不到准确的现成词语来表达、描述,所以不得不自造词语。(当然,有的时候也是因为不愿用熟词写作。)
即便现在,李贺诗歌仍是我的至爱。
当我读到张杰近3年来的诗歌时,除了意识到他已“由蛹化蝶”、获得新生外,还马上想起了李贺。这里我随意举两首李贺的诗歌:
《秋来》
桐风惊心壮士苦,衰灯络纬啼寒素。
谁看青简一编书,不遣花虫粉空蠹?
思牵今夜肠应直,雨冷香魂吊书客。
秋坟鬼唱鲍家诗,恨血千年土中碧。
《古悠悠行》
白景归西山,碧华上迢迢。
今古何处尽,千岁随风飘。
海沙变成石,鱼沫吹秦桥。
空光远流浪,铜柱从年消。
可以看出,张杰近3年来的诗歌和李贺的诗歌何其相似:两者都不用常语熟词写作,而是别开生面,求奇出新,用词奇炫、奇峻、生僻、变幻,修辞雕饰而讲究,使诗歌生成“新体”,最终别成一家。
虽然张杰的诗歌和李贺的诗歌诗体相异,张杰的冷静、沉实也有别于李贺的奇崛、峭拔,但凭着张杰近3年来的近百首不同平俗、风格卓异的诗歌,我可以不太夸张地说:“蝶化”之后的张杰无疑已是一个当代“李贺”。
并且,凭着我对张杰的了解,我知道他并未关注李贺,他也未学李贺,他对词语的创新、语言的更新,完全来自他天生的对语言的敏感、悟性,和他性格中的某种偏执、不能忍受平俗的心性、勇于创生的胆魄、勇气。他在“北京时期”就已开始自觉地在更新诗歌语言(只是那时我并未认识到他这样做的意义,加之我自己内心的骄傲,所以平日对他的诗歌常常感到不屑),其后经过了10年漫长的探索、试验。到2014年春天时,他的诗歌出现了崭新的变化。而经过他执著的探索,坚持不懈的努力,他终于写出了现在的“别成一家”。所谓“无心插柳而成荫”,他没有学李贺,然而却和李贺“殊途同归”,成为了一个当代“李贺”。
可以说,正是有了张杰的“蝶化”,有了张杰3年来的这近百首不同平俗、风格卓异的诗歌,张杰才成为了张杰,就如李贺之所以成为李贺一样。
张杰在世俗层面是单纯的、简单的,但其心中却似装有万壑,胸中蕴藏着天地之灵气、峻气,其诗中已多有峻拔、腾耀、神妙之语句:
“内心的水管,还没有冻住,在颈部滴答,
幻想去开雾的铁门。”
“浓雾的不透明,把我们抱进隔离的幻境。
白雾撞击、覆盖我们时,踩着温柔的脚刹。”
——《冬的白雾》2015.12
一个黄昏的黑洞,正路过我们,像颗星际行星,
视界之内,我们看到完全不同的毁灭。
——《给黄昏》2016.6
闪耀的下午在高空平坦滚动。
百年难掩的空落。
——《丁酉初春下午》2017.04
你的天文镜会自动寻星
看到的世界会叠加、锐化
那里,冬的黄昏在小山上望乡
西南方土星在闪光
——《霾中》2017.1
他这批诗歌的题材是足够丰富的,有咏物、抒怀、感时、咏史、讽世、记游、记行、题赠等等。他对时代的思考、历史的辨识、世界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奥,有时他对世界和宇宙真相的揭示令人撼动:
细胞将在死亡之界的统御里,四处飘散。
嘈杂城区,静悄悄生长边塞的荒凉,
要获得的只是世间长廊里的空。
原来获得的,不在这里,也不在那里。
——《春天的太阳即是爱的骑士》(二)2017.02.26
世界像脏钻石
谁对古怪北原有所了解?
谁在继续封闭与教条,谁在继续批判?
北原的错,上可追溯到秦国的君臣
下可悬停在此,过多的罪恶,缺陷,瑕疵
破裂的天空,强烈的信号,无数的碎片
旋转那仍不忏悔的机器
那永恒无误准确的钟,并不存在
——《北原》2016.10
当然,张杰的诗歌还不完美,个别诗歌还有明显的缺陷,比如他偶尔会将一首诗任性地拉长,缺少节制,显得冗长、累赘而无必要;个别诗歌在一个音调上平行滑动,缺少起伏,等等。但张杰毕竟还是一只“新生的蝴蝶”,有他早期和近期的这么多的优秀诗歌作为佐证,我们有理由也有信心,期待:他的成长,他的生光。
相关推荐
友情链接
Copyright © 2023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北京物流信息联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