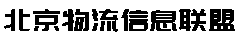
2021-12-23 08:45:24
添加补漏客个人微信号:nj13951746173,可获更多分享
原文标题:重新认识“合同”与“公司”—基于“对赌协议”类案的中美比较研究
[摘 要]:我国“对赌协议”纠纷裁判中,对于投资者与公司之间现金补偿与股权回购约定的效力,理论与实践存在争议。美国Thoughtworks案与我国此类“对赌协议”纠纷构成类案。案例比较研究着眼于普遍性问题的解决,尤为符合比较法的功能性原则。基于与域外类案的比较研究,将与强制性规范关联的合同效力问题压倒性地作为核心甚至唯一争点的合同逻辑应予改变,应实现合同效力与合同履行的区隔,将公司因资本规制不能支付补偿或回购款的问题在依托于公司法机制的履行障碍违约责任承担的逻辑下展开。相应地,应改变将公司作为股东财产延伸的理解,重视公司的组织属性,贯彻董事会中心主义,并由市场中介为董事会决策提供坚实的程序性支撑。
[关键词]:对赌协议;类案;合同效力;合同履行;董事会
一、引言:争议中的“对赌协议”纠纷裁判
“对赌协议”作为一种定价机制,旨在回应融资方与投资方在企业估值方面的分歧。它体现为根据被投资企业未来业绩等指标,在高估企业时由融资者补偿投资者,在低估企业时由投资者补偿融资者。从“对赌协议”纠纷裁判揭示出的条款设计来看,目前我国“对赌协议”的交易结构主要体现为投资者先期进行溢价投资,并设定一定的业绩或上市目标,如果未能实现这些指标,由原始股东或被投资公司对投资者进行现金补偿或回购投资者持有的股权,也存在由原始股东向投资者补偿股权的情形。
美国是风险投资的大本营,但并未在其风险投资合同示范文本[1]或相关文献中发现“对赌协议”或“估值调整机制”的对应条款安排。与“对赌协议”近似的是企业并购中的earnout条款,国内通常将其翻译为“盈利能力支付计划”。其大致的构造是收购方在并购交易交割时仅支付并购价款的一部分,其余部分根据被收购企业在并购完成后的业绩支付,其功能在于解决并购交易双方在企业业绩预期以及定价上的分歧。[2]这一定价机制普遍存在于非上市公司并购中,[3]交易方“赌定其预期的准确性,只有在不确定性消除、双方真正拥有共同的确信之后才会了结”。[4]国内的“对赌协议”与美国的earnout条款仍存在两个重要区别:其一,适用的领域不同。earnout是并购交易中的定价机制,“对赌协议”存在于风险投资或私募股权投资中。其二,交易结构的具体设计尤其是资金的流动方向不同。earnout是先支付一部分价款,其余部分视企业未来业绩支付;“对赌协议”尤其是目前普遍存在的情况则是先支付全部价款,在企业无法完成业绩时由融资方补偿或回购投资方。这一区别带来了不同的法律规制,earnout的主要问题在于条款的解释尤其是收购方干扰、操纵业绩目标的实现等机会主义行为,[5]而“对赌协议”则可能触发公司资本管制。
我国实践之所以将并购交易中的定价机制应用于日常融资,并做这样一种反向设计,或许归结于以下两点原因:其一,我国公司立法缺少对优先股的支持。美国风险投资实践普遍以可转换优先股作为投融资工具。[6]优先股扩张了普通股的某些财产性、治理性权能,如反稀释保护、回赎权、领售权、清算优先权、一票否决权、董事席位数等,从而契合了风险投资家的投资偏好和风险管理需求。其二,受制于投资基金存续期限过短的“快VC”与“赚快钱”“全民PE”下的专业性欠缺与投资经验匮乏、大量资金追逐少部分“明星”项目背后的尽职调查粗糙与竞相抬高项目估值,[7]这些市场条件可能使投资者难以作出earnout中的细致安排,从而将“对赌协议”中的事后补偿或回购作为主要甚至唯一的风险控制工具。
由于通过合同手段打破了标准的公司利益与风险分配格局,“对赌协议”纠纷中的合同法问题与公司法问题交叉错位,成为我国商事审判与仲裁实践中的疑难与突出问题。其中,原始股东对投资者进行现金、股权补偿或者回购股权的情形,理论以及实务上较少存在争议,基本达成了属于股东之间契约自治的共识。而被投资公司以现金补偿投资者或者回购投资者股权的情形,则备受争议,理论与实践莫衷一是。
被称为“对赌协议第一案”的甘肃世恒有色资源再利用有限公司、香港迪亚有限公司与苏州工业园区海富投资有限公司、陆波增资纠纷案[8](以下简称“海富案”)中,涉诉“对赌协议”约定了未实现业绩目标时被投资公司对投资者的现金补偿条款。该案再审判决认为这一约定使投资者“可以取得相对固定的收益,该收益脱离了世恒公司的经营业绩,损害了公司利益和公司债权人利益”,进而判定这一条款无效。继“对赌协议第一案”之后的司法与仲裁实践并未形成一致的裁判思路与分析框架。在山东瀚霖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曹务波与公司有关的纠纷案[9](以下简称“瀚霖案”)中,,为无效。但与“海富案”不同的是,。仲裁实践中则出现了“逆转”裁决,在部分案件中,仲裁庭确认了被投资公司与投资者之间现金补偿条款与股权回购条款的效力。[10]
“无效”是对合同自治的彻底否定,风险投资又高度依赖于合同秩序,司法实践的做法遭到了理论上的诸多质疑和批判。学界的反思始于“对赌协议”交易结构及其功能的分析,认为“海富案”判决误解了估值调整的交易实质,进而主张“对赌协议”的有效性。[11]理论研究大致分为合同法进路和公司法进路两类。其一,合同法方面,“对赌协议”是无名合同,在对此种合同安排还比较陌生的情况下,关于合同性质的厘定是展开私法分析的习惯性思维,存在射幸合同、期权合同、附条件合同等不同看法。[12]实际上这一问题在“海富案”之前已经引起学者关注。[13]但某一合同性质的给定并不必然意味着法律的保护。如果认为在被投资公司业绩承诺兑现之前,投资溢价款是公司对投资者的负债,投资者的股权也并非公司法意义上的股权范畴,“对赌协议”问题就被框定在合同层面,从而适用合同法原理而非公司法原理对合同效力予以判断。[14]此外,合同法领域“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等问题的讨论,尤其是近年来合同自治与公司自治的伸张形成了法律管制与契约自治的制度与思维惯性,受这种惯性的影响和制约,一部分讨论集中在检讨公司法资本管制与债权人保护规则是否为合同法中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15]其二,公司法方面,由于被投资公司对投资者的补偿或回购触发了公司资本管制,研究大多沿着资本规制的分析路径展开。通过展示Thoughtworks,认为在法官专业化的基础上,通过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具体分析来判断“对赌协议”履行的可能性才应当是司法裁判的核心;[16]或认为我国公司法的资本规制过度,增加了对赌实践的交易成本,且“对赌协议”的法律效力应根据其采取的减资、回购、分配等法律机制具体分析。[17]
既有的争论游走在契约自治、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债权人保护、资本维持等私法范畴之中,对问题的讨论正在逐步逼近事物的本质。发现问题的出路仍须检讨一些基本的、前提性问题,进而更新思维模式。通过对比较点的甄别和分析,美国特拉华州Thoughtworks案与我国“对赌协议”纠纷构成类案。面对类似的争议问题,两国司法实践提供了迥异的处理方案、分析框架和裁判思维。这背后蕴含的是这样一个前提性问题:如何认识“合同”与“公司”?厘清这一问题,将进一步回答合同如何约束和遵守,公司如何治理与行动,组织逻辑与契约逻辑如何相互嵌入,组织秩序与契约秩序如何共生等冋题。
二、作为“对赌协议”纠纷类案的美国Thoughtworks案
(一)Thoughtworks案[18]的事实与判决
2000年,原告SVIP以优先股的形式向Thoughtworks公司注资2660万美兀,Thoughtworks公司章程赋予了SVIP要求公司回赎其股份的权利。这一回赎权利在注资五年后方可行使。关于公司回赎股份的资金来源,章程的表述为“合法的可利用的资金”(funds legally a- vaikble)。回赎价格为股份的清算价格(计算公式为初始购买价格+累积未分配红利+视为已转换为普通股的前提下与普通股股东按比例分配公司剩余资产)或公允市价中的较高者。之所以设置该项权利,在于SVIP期待Thoughtworks将实现公开上市,如果Thoughtworks未能上市,SVIP可主张回赎权利退出公司,以收回投资。同时章程规定,公司的回赎义务是持续性的。也就是说,如果届时Thoughtworks没有足够的“合法的可利用的资金”以满足回赎要求,无需优先股股东进一步的权利主张,公司后续符合条件的资金将用于回赎股份,直至回赎义务履行完毕。
然而,伴随着互联网泡沫的破灭,Thoughtworks公开上市的目标已无望实现,SVIP遂于2005年主张回赎权利。在寻求法律与财务建议后,Thoughtworks董事会决定遵循以下程序、条件计算可用于履行回赎义务的“合法的可利用的资金”:用以回赎的资金不得超过公司盈余;不损害公司的持续运营能力,不削弱任何公司资产的价值,因为资产在清算中的价值会远远低于其作为存续企业一部分的价值;避免做出将导致企业资不抵债的决策……基于此,2006年8月,董事会决定回赎价值50万美元的优先股。在此之后的16个季度中,Thoughtworks董事会在每一季度遵循相同的条件和程序决定公司用于回赎股份的“合法的可利用的资金”,并累计回赎了价值410万美元的优先股。Thoughtworks也曾为回赎向第三方融资,一家私募股权基金曾表示出借2500万美元用以回赎优先股,前提是优先股股东交出所持全部股份,但遭到SVIP拒绝。
,无论是特拉华州普通公司法还是判例法,其基本立场是公司回赎股份不得削弱公司资本、损害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或招致公司资不抵债,从而保护公司债权人。实际上,“合法的可利用的资金”或者类似的术语常见于关于回赎或者分红的章程条款。即使有关条款遗漏了这一表述,法律也会对公司回赎作出类似限制。对于Thoughtworks董事会所决定的“合法的可利用的资金”的数量,原告必须证明董事会恶意、依据不可靠的方法和数据或者其决定极不中肯进而构成实际的或者推定的欺诈,才得推翻这一决定。
,在本案中,原告通过现金流量贴现、同类公司以及同类交易的方法计算出Thoughtworks的股本价值在6800万—1.37亿美元之间,从而认为这就是Thoughtworks“合法的可利用的资金”,并要求原告支付66, 906, 539美元回赎款,在此原告并没有考量如何使Thoughtworks在履行回赎义务的同时仍能够持续经营。本案事实表明,Thoughtworks董事会秉承最大善意,并依据专家的详细分析做出决定。在16个季度中,董事会就“合法的可利用的资金”的数量作彻底调查,并以此回赎优先股。在每一个场合,董事会咨询财务与法律顾问,了解公司经营现状,慎重权衡在避免威胁公司持续运营能力的前提下可用于回赎优先股的资金数量。同时,董事会还积极地在市场上检验公司可获得的用于回赎优先股的资金数量。而借款方的出价则是证明公司合法可利用资金的最大数量的最可信证据。基于此,SVIP的诉讼请求。
(二)为什么构成类案
类案判断的前提在于比较点的选择,[19]即争议问题类似或具有同类性,而争议问题又兼有事实性和法律性。[20]Thoughtworks案与我国“海富案”“瀚霖案”等“对赌协议”纠纷的争议问题具有类似性,构成类案。
第一,三则案例处于相同的行业背景,均产生于风险投资实践。行业背景影响了交易方的动机,进而决定了特定的交易构造。风险投资实践中,投资者对被投资公司寄予了高增长、高利润的期待,例如三则案例中的投资方均期待公司实现上市。这种类型的投资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因此投资者具有更强的风险管理需求。
第二,三则案例中与争议问题关联的关键事实类似。“海富案”中,由于公司未能达到利润指标,投资者要求公司进行现金补偿;“瀚霖案”中,公司达不到利润指标和上市目标,投资者要求公司回购股权;Thoughtworks案中,公司无法实现上市,投资者要求公司回赎股权。值得说明的是,风险投资实践中,在被投资公司未能实现预期目标时,投资者要求公司进行现金补偿与回赎股权的效果具有同一性。其实质都是投资者通过从公司获得现金以收回投资、退出公司。因为此时大量资金从公司流出,公司发展将受到重创。即使是在投资者仍保留公司股权的情况下,公司股权的价值已大大贬损,且继续作为股东的投资者与原始股东的关系通常会因为回赎股权而恶化。
第三,三则案例中与争议问题关联的法律适用类似。35条禁止抽逃出资、37条减资须经法定程序以及第74条公司应股东请求回购股权的法定情形的规定;Thought- works案则申明“公司回赎股份不得削弱公司资本、损害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或招致公司资不抵债,从而保护公司债权人”。这些本质上都是公司债权人保护、资本维持之类的法律规定。
第四,Thoughtworks案与我国此类“对赌协议”纠纷的事物本质类似。“所谓类比推理的某些规则,是那种融合了生活正义和规范正义(价值与法律)的一般性的认识,即事物的本质。”[21]被投资公司以现金补偿投资者或者回购投资者股权,究其实质,是公司与股东之间的资本性交易。[22]与投资者向公司出资这一公司法人财产与股东有限责任的生成逻辑相比,资金从公司逆向流入股东,公司用以维持经营与满足债权的资产减少。相应地,无论是美国的Thoughtworks案还是我国的此类“对赌协议”纠纷,问题的本质都在于公司资产减损的此种威胁能否阻断公司资金向股东的逆向流出。
第五,Thoughtworks案与我国此类“对赌协议”纠纷的事实差异不足以推翻类案的判断。首先,“海富案”与“瀚霖案”中,投资者均进行了溢价投资。Thoughtworks案虽然未表明溢价投资的事实,但从判决书的描述来看,被投资公司提供“信息技术专业服务”,“员工是最有价值的资产”,投资者对被投资公司的估值严重依赖无形资产的事实将该投资与普通投资区分开来。而且投资者与被投资公司在估值方面存在分歧,尽管投资者认为其已充分估价,被投资公司却相信即使是选择相对保守的退出策略,这一交易也将带来富有吸引力的回报。最终的合同条款安排(尤其是回赎权条款)建立在双方对近一两年公司实现上市的预期之上。其次, Thoughtworks案中,公司的回赎义务被设定为持续性义务,且公司已经回赎了部分优先股。但这一事实并未妨碍投资者提出支付全部回赎款或者重新定义“合法的可利用的资金”的请求,不妨碍对案件争议问题的判断。当然,未将回赎义务设定为持续性义务,未作回赎义务到期、公司财务状况可能无法一次性支付全部回赎款的预计和事先安排,反映了我国与资本市场发达国家在商主体缔约能力、商事实践成熟程度方面的差距。
(三)案例比较研究的方法及其局限
“全部比较法的方法论的基本原则是功能性原则,由此产生所有其他方法学的规则——选择应该比较的法律、探讨的范围和比较体系的构成等。”[23]案例比较研究作为“基于事实的研究方法,它在各具体实践知识具有同一性的基础上进行归纳总结”。[24]之所以是一种科学的方法,在于其着眼于普遍性问题的解决,而不是拘泥于不同法域的概念与规范,尤为符合比较法研究的功能性原则。“晚近的比较民法学家不再将制定法和概念体系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而更关注法律实践活动,尤其是一国司法机关的裁判或判例。”[25]其中,对案例的分析应“在中度抽象的意义上”,[26]使用一种更为包容、具有普适性[27]的范畴体系和分析框架,进而达成对我国制度构造和制度运行的深刻理解与批判反思。[28]
将案例作为比较法研究的对象,基于不同的研究目的,可以有不同的角度和方法。本文关注的是,既然域外类案的争议问题类似,对于不同法域面对的普遍性问题,司法机关对问题的理解和定位、所提供的问题解决方案有何差异?这些差异体现了问题分析框架与裁判思维模式的何种差别或差距?在本文的语境下,针对回应投资风险管理需求的交易策略,司法实践中公司经营及债权人保护的考量如何影响资金从公司到股东的逆向流出?在如何认识“合同”与“公司”、合同如何被尊重、公司如何采取行动、契约逻辑与组织逻辑如何交互影响这些前提性、基本性的问题上,两国司法实践的认知有何本质差异?这一本质差异又如何影响对具体问题的分析和判断?
针对案例尤其是个案的比较研究,在方法上仍存在风险和局限性。它必须首先回答选取的案例在特定法域中是否具有代表性,是否是特定法域的主流做法,其次,司法裁判作为法律的实践活动,有其特定的时空、制度乃至体制背景的约束。因此需要回答案例比较研究导出的发现或者结论如何具有在另一法域中的适用性。
第一,就Thoughtworks案本身而言,它无疑是美国优先股赎回权的新近代表性案例。在此之前,这一问题的代表性案例要追溯到1942年新泽西州的Mueller v. Kraeuter & Co.案。[29]旧有的案例并不清晰,而且制度上已经过时。[30]实际上,Thoughtworks案正是法官将优先股制度重新嵌入公司法框架的一次努力,因为Mueller案判决的七十年之后,司法审查已经转移到董事的决策程序而非决策内容本身。[31]Thoughtworks案至今也并未遭遇司法实践的否定性对待。[32]《宾大法律评论》上曾经出现过公司法学者与特拉华州法官之间就该案的论战,争论主要集中在对优先股股东回赎权利行使的限制以及通过事前缔约消解权利行使的不确定性等问题上,[33]但这些争论并不能否定Thoughtworks案的代表性。改写美国公司法历史的标志性判例,如Dodge v. Ford、[34]Smith v. Van Gorkom、[35]Basic Inc. v. Levin- son[36]等无不经历了激烈论争。
第二,Thoughtworks案出自特拉华州,特拉华州在美国公司法上居于引领地位,但这一现象也遭到了“底线竞争”的质疑。怀疑者担忧“各州为了吸引发起人、控股者、管理人员,从而在规则上倾向于管理者,管理者则希望排除找麻烦的股东、政府机构、,就会忽略:……小股东的保护……”。[37]Thoughtworks案的确贯彻了董事会中心主义和商业判断规则,但这并未以牺牲小股东利益为代价。Thoughtworks董事会在支付决策中努力平衡公司利益、债权人利益、普通股股东利益、优先股股东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好的、有效率的、平衡各方利益的公司法”。[38]
第三,Thoughtworks案的裁判依托于诸多美国公司法制与公司实践的元素,例如董事会中心与商业判断规则中的董事权力、趋严的董事高管诚信义务下宽松的资本规制、[39]与生硬的股权债权的概念区分相对的灵活性和诚信义务的扩展、[40]发达的市场中介以及法官驾驭商事交易的能力。由此本文的案例比较研究在思维层面的意义可能大于操作层面的意义,但通过比较揭示出的思维模式上的差异是不同裁判思路和方案的根源和前提所在。
三、重新理解合同逻辑:合同效力与合同履行的区隔
(―)我国“对赌协议”纠纷裁判的合同理路:合同效力与强制性规范
我国“对赌协议”纠纷裁判及其在业界引起的争论表明,目前我国商主体与商事法官对“对赌协议”纠纷的理解集中在合同条款的效力问题,并将其与公司法强制规范相关联。在某机构发布的研究报告,[41]提及的18份“对赌协议”“典型案例”裁判文书中,剔除原审认定事实不清、发回重审的情况[42]以及案件争议实质上与“对赌协议”的合同内容无关的情况,[43]本文共得到16份有效的裁判文书。[44]在这16份裁判文书中,仅有1份不涉及“对赌协议”的效力问题。[45]也就是说,93.75%的“对赌协议”纠纷被定位为或者部分定位为“对赌协议”的效力问题。在论及该问题时,无论是有效判决还是无效判决,基本上均以“不违反法律、。[46]至于关联于合同效力的强制性规定,多援引公司法关于债权人保护、资本维持原则的强制性规定。[47](参见表一)
表一“对赌协议”典型案例的效力判断及其依据
“对赌协议”以合同手段改变公司格局,我国商事审判在公司法问题与合同法问题的交叉错位中,将自由与强制的矛盾作为纠纷裁判的重心。并且,合同效力问题压倒性地成为核心甚至唯一争点,裁判过程在有效抑或无效的非此即彼的判断之下展开。这种僵化的处理方式使商主体的自治与公司法的管制难以共存,从而最终使自由与强制的矛盾无法调和。
(二)合同效力与合同履行相区分的民法依据
合同效力与合同履行的区隔源于民法上的区分原则,即“在依据法律行为发生物权变动时,物权变动的原因与物权变动的结果作为两个法律事实,它们的成立生效依据不同的法律根据的原则”。[48]这一原则又是基于民法体系中请求权与支配权、债权与物权、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的区分。[49]由此,以权利变动为目的的基础债权合同与作为合同履行法律效果的权利变动本身是两个相互独立的法律事实,[50]合同效力与合同履行是不同的问题层次。区分原则在我国民事立法中有所体现。例如《物权法》15条规定:“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值得注意的是,,如《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16条规定“如果强制性规范规制的是合同行为本身……,。如果强制性规定……规制的是某种合同的履行行为而非某类合同行为,,应当慎重把握……”。
区分原则意味着,对合同履行的干预和制约独立于对合同效力的判断和评价,合同履行所遭遇的法律上的障碍不应影响合同的效力状态。具体到“对赌协议”纠纷,对于公司与股东之间股权回购或者现金补偿的约定,公司资金逆向流入股东是权利的变动,是履行基础债权合同的合同履行行为。基于此履行行为的债权人保护、公司资本维持的考量不应影响合同的效力评价,仅仅是可能构成合同的履行障碍。在此并非置公司法原理与规则于不顾,而是将这些因素框定在合同履行阶段而非前置于合同效力的评价阶段。厘清合同效力与合同履行的问题层次有助于兼顾契约自治、机会主义行为的防范以及公司法的规范目标,是一种更优的规制策略。
首先,将合同效力的评价与合同履行行为区隔开来将为交易工具创新释放更大的自治空间。以合同履行阶段的规范考量为依据否定合同效力,将“一刀切”式地推翻商主体利益与风险分配的契约自治。对于财务状况良好、回购股权或补偿现金不会损及债权人利益与资本维持的公司,没有理由否定公司与股东之间股权回购或者现金补偿约定的效力,迫使商主体改变交易安排,将“对赌协议”局限在原始股东与投资者之间。
其次,将合同效力的评价与合同履行行为区隔开来有利于防范机会主义行为。与合同履行阶段强制性规范关联的合同无效机制,不仅僵化地否定了商主体的权利义务安排,也可能会被合同债务人利用,成为逃避合同有效前提下合同义务履行或者违约责任追究的极为便捷的抗辩。
最后,合同效力与合同履行的区隔创造了一种弹性的合同法律机制。在这一分析框架下,不同于单一合同无效机制中自由与强制的无法调和,合同有效支撑起的契约自治与合同履行阶段的法律管制得以共存,商事实践中无限可能的利益状态得以被讨论和包容。
(三)“对赌协议”履行障碍的违约责任承担
Thoughtworks案中,,均未涉及回赎权条款的效力问题,而是在合同履行的层面上,以公司经营和债权人保护为依据定义“合法的可利用的资金”。,驳回了由公司支付全部回赎款的诉讼请求。由于公司章程将公司的回赎义务界定为持续性义务,虽然目前没有足够的“合法的可利用的资金”以满足回赎要求,但公司后续符合条件的资金将用于回赎股份,直至回赎义务履行完毕。
在我国“对赌协议”纠纷中,以“海富案”和“瀚霖案”为例,合同并未将现金补偿或股权回购义务设计为持续性义务,公司因资本维持的需要不能支付补偿或回购款的情况构成履行障碍。由于现金补偿或股权回购义务为金钱债务,不存在履行不能的问题,此处构成合同法上的履行迟延。[51]在此,作为债务人的公司并不存在免责事由。这是因为,投资者与公司之间的投融资交易具有高风险、高度不确定性的特质,在此背景下的“对赌协议”其功能在于估值调整,是投资风险管理的手段,是投融资双方基于投资特性充分协商和议价的产物。通常情况下,如果公司没有实现约定的业绩指标,属于正常的商业风险,债务人公司对于此种风险充分知晓,可以理性预测,并非不可抗力或情事变更。[52]因此,在认可“对赌协议”有效性的前提下,债务人公司因公司法上的资本规制不能支付补偿或回购款的问题应在履行障碍的违约责任承担逻辑下展开。
违约责任是对履行利益的赔偿,“被害人得请求赔偿者,系债务人依债之本旨履行时,其可获得之利益”。[53]基于公司的独立财产、拟制人格与既定程式,强制履行等合同救济方式在公司中存在适用的边界。[54]于此,公司实际履行支付补偿或回购款的违约责任承担方式存在基于公司资本规制的法律障碍。借鉴Thoughtworks案中公司支付回赎款的方式,应在合同有效的前提下实现违约责任承担方式的灵活性与多元化,并综合运用合同法与公司法、实体法与程序法机制,可以基于公司的财务状况,在资本维持的前提下延期或分期支付补偿或回购款,直至满足投资者的履行利益。在确定补偿或回购款的支付期限和支付金额方面,Thoughtworks案又集合了证明责任的分配与转移(董事会与股东之间)、。这些机制的运用在公司法中展开,其理论前提是公司法对公司的理解和定位。
四、重新理解公司逻辑:从财产到组织
(一)我国“对赌协议”纠纷裁判的公司理路:作为财产的公司
公司是什么?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存在“财产定义”(property conception)与“实体定义”(entity conception)两种模式。前者将公司作为股东的私有财产,后者将公司作为一个社会机构。[55]从“海富案”与“瀚霖案”的判决说理和所援引的公司法律条文来看,我国“对赌协议”纠纷裁判的公司法路径在于将公司作为“股东财产延伸”,[56]忽视了公司的组织属性。
“海富案”援引了《公司法》20条“公司股东……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瀚霖案”援引了《公司法》35条禁止股东抽逃出资、第37条减资须经股东会决议通过以及第74条公司应股东请求回购股权的法定情形的规定。这些规则的共性在于以股东利益为出发点,以股东行为为中心,通过股东规范公司行为。但公司作为组织,“本质在于社团性,而社团意志的特点在于程序,是由公司治理所确立的决策过程”。[57]判决并未在组织的框架下,将特定的投融资交易中公司以现金补偿投资者或者回购投资者股权作为公司组织的决策事项,诉诸特定的决策主体和决策程序,并由特定的决策机构对决策负责。这一逻辑的缺位是公司“财产模式”的体现,公司沦为融资手段,是股东所有权之派生,强调股东利益通过公司的实现,“谁投资、谁所有、谁受益”。[58]
在“瀚霖案”中,4200万元及其资金成本的诉讼请求。这一立场是基于投资者对被投资公司进行溢价增资,在4900万元的投资款中,只有700万元计入注册资本,其余4200万元进入被投资公司资本公积金的案件事实。其逻辑在于投资者不能抽回股本,但作为溢价增资部分的资本公积金可以返还给投资者,而“海富案”却并未持此立场。“海富案”同样存在投资者溢价增资的事实,但再审判决并未将投资款作股本与资本公积金的区分讨论,而是一概否定公司向投资者支付补偿款、资金从公司到股东的逆向流出。是否允许公司将资本公积金返还给投资者,我国立法并不明确,在有的公司立法中,公司对股东的无偿支付若出自资本公积金,也构成抽逃出资。[59]实际上,公司的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等具体财务状况随着公司经营持续变动,即使公司向股东支付的数额与计入资本公积金的溢价增资款数额相当,也并不必然说明公司对股东的支付来源于资本公积金,其有可能来自盈余公积金,也有可能来自未分配利润,当然也有可能是抽逃股本。显然,除了最后一种情况,前两者并不危及公司债权人利益。拋开公司立法对资本公积金返还的态度问题,“瀚霖案”与“海富案”均未具体分析公司的财务状况,更没有在公司组织的框架下、在公司决策程序中展开对资本维持的讨论,而是将公司视作静态财产,判决说理过于僵化和武断。
(二)公司组织中的董事会中心主义
与我国“对赌协议”纠纷裁判中的公司“财产模式”不同,Thoughtworks案判决在组织的框架下展开。公司应否履行支付全部回赎款的义务被定位在董事会决定的公司用以回赎投资者优先股的“合法的可利用的资金”的数量这一问题上。原告投资者诉求的伸张只能通过推翻Thoughtworks董事会的决定来实现。原告承担“董事会恶意、依据不可靠的方法和数据或者其决定极不中肯进而构成实际的或者推定的欺诈”的证明责任。,当董事会决定可用于支付回赎款的盈余数量时,只要不存在上述情况,其决策应被尊重。也就是说,,对董事会决策的审查集中在董事会的决策程序,避免介入决策的实质内容。funds legally available)等同于“盈余”(surplus),[60]但法庭并没有替代Thoughtworks公司董事会作出商业判断,而是详细分析了Thoughtworks公司董事会的决策依据和过程。对于投资者一方提交的关于Thoughtworks公司“合法的可利用的资金”的专家意见,、依据不可靠的方法和数据或者其决定极不中肯进而构成实际的或者推定的欺诈这一问题的分析提供任何帮助”。
在Thoughtworks案中,一方面,董事会的决策具有充分的依据。董事会依据法律与财务顾问的建议以及公司经营现状,在每一季度遵循一定的程序和条件计算可用于履行回赎义务的“合法的可利用的资金”。另一方面,董事会也曾通过市场中介为回赎寻求资金。其财务顾问Alix Partners发出了70份信息备忘录。一家私募股权基金曾表示出借2500万元用以回赎优先股,前提是优先股股东交出所持全部股份,但遭到投资者拒绝。这些事实使Thoughtworks。
Thoughtworks案的判决说理尊重了公司的组织属性,贯彻了公司组织中的董事会中心主义。依据董事会中心主义,董事会并不仅仅是股东的代理人,而是组成公司的各种合同的中心。[61]与董事会中心相对的股东中心,其核心依据在于股东是公司的剩余索取权人。实际上,除了在破产的语境之下,声称股东是在公司其他利益相关者获得固定回报后取得公司剩余收益的说法是极具误导性的。公司作为法律实体,是其自身的剩余索取权人,是其利润的所有者。债权人、员工、供应商甚至税收机关的利益既非固定,又非稳定。在有偿付能力的公司中,商业判断规则赋予了董事会自由裁量权,它可以随时提高员工工资福利、更为慷慨地对待供应商、留存收益从而给予债权人更多保障或者拒绝采取积极的避税策略。[62]而股东仅仅有权获得董事会依其商业判断宣布发放的股利。因此,股东作为公司的剩余索取权人以及股东中心说具有相当的局限性。同时,公司内部的三大冲突——经营者与股东之间、股东相互之间、股东与公司其他利益相关者(包括债权人和职工)之间的冲突被概括为“代理问题”。[63]股东中心看似降低了经营者与股东之间的代理成本,但事实却是,“这些代理成本的大小相互关联,其中一种代理成本严重程度的变化会对其他代理成本的严重程度产生影响”。[64]股东中心会带来债权人利益遭受威胁、其他利益相关者蒙受不利、公司经营短视等一系列问题。[65]
之所以赋予董事会最终决策权力,将董事会作为公司治理架构的中心,尊崇董事会的权威,究其实质,在于公司中任何一方的专用性投资对于公司生产的重要程度都不足以使其占据统治地位时,独立于任何公司团队成员的董事会权威将鼓励所有成员的专用性投资。于此,董事会发挥了协调成员活动的功能。而当某一方的专用性投资居于压倒性的地位时,董事会权威将失去意义。[66]团队生产理论对董事会权威的这一阐释能够有效解释在类似于Thoughtworks公司、我国与投资者签订“对赌协议”的公司中,尊崇董事会中心地位的意义。在这些公司中,由于部分投资者享有的优先权利(回赎权、现金补偿权利等),投资者持有的股权或股份实际上被划分成了不同类别,不同类别股股东的利益诉求具有了异质性。公司股东的异质性使得股东无法再作为一个整体占据公司团队生产中的统治地位。任何一类公司团队成员的专用性投资都无法居于压倒性地位,这就产生了对董事会协调功能、董事会权威的需要。“类别股股东作为一股重要的外部投资力量,将推进股东会中心主义向董事会中心主义的转变。”[67]同时,尽管相对于优先股股东,普通股股东没有针对公司财产的优先权利,但由于公司经营的不确定性,最大化普通股股东的价值并不一定能够实现公司价值的最大化。[68]此时,董事会发挥协调功能、享有最终决策权力对于公司团队而言是最具效率的。
(三)公司组织的看门人:市场中介
Thoughtworks案中,影响判决结果的一个重要案件事实是公司董事会为回赎股份,专门聘请了法律以及财务顾问,[69]其法律顾问向董事会提供了决定可用于履行回赎义务的“合法的可利用的资金”的具体程序;其财务顾问除了在上述方面给出专业建议,还为回赎寻求资金,代表Thoughtworks公司发出了70份信息备忘录。其中,一家私募股权基金表示出借2500万美元用以回赎优先股,前提是优先股股东交出所持全部股份,但遭到投资者拒绝。对此,,董事会还积极地在市场上检验公司可获得的用于回赎优先股的资金数量,而借款方的出价则是证明公司合法可利用资金的最大数量的最可信证据。从而诉诸市场逻辑,将市场专业中介机构在一定程序下获得的市场报价作为董事决策、。
“对于研究公司治理的学者而言……他们一直在永无休止地探讨着董事会和股东的问题。……但它留下了一个重要盲点。它忽视了金融市场中各种专业机构的角色和功能……。”[70]市场专业中介机构除了上述的律师、金融咨询机构外,还包括审计师、证券分析师、资信评级机构等。在资本市场发达国家,董事决策、公司行为依赖于市场中介的信息、建议以及中介服务。市场中介机构以其专业性和在资本市场中的声誉保障了董事决策的理性和善意,作为董事决策的重要程序,市场中介的介入也为董事的免责提供了有力支撑。基于其对公司治理的监督功能,市场中介被形象地称为“看门人”(gatekeepers),其角色至为关键,以至于有学者认为“董事会都是其看门人的囚徒”。[71]
市场中介的上述功能在我国“对赌协议”实践中则是缺位的。“海富案”的裁判文书并未体现市场专业中介结构的介入。“瀚霖案”中,被投资公司的财务状况由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但仅局限于证实公司的净资产值以及净利润数额,也未体现市场中介对公司回购决策的影响。与之相关的是,我国“对赌协议”实践中,投资者与被投资公司签订“对赌协议”时,往往没有进行全面的尽职调查。在“资金多、好项目少”的局面下,被投资公司漫天要价,在给出对公司的超高估值后,投资者再依赖“对赌协议”中公司或其原始股东的补偿来控制投资风险。[72]与Thoughtworks案中法律顾问、财务顾问等市场中介为董事会决策提供坚实的程序性支撑相比,我国的“对赌协议”实践缺失了以专业中介作为公司组织“看门人”的市场逻辑。
五、结语:进一步回归市场逻辑的商事审判
关于“对赌协议”纠纷裁判立场的争议仍在继续。[73]合同与组织是市场配置资源的两种重要方式,“对赌协议”以合同手段重置了公司组织中的利益与风险。基于对合同逻辑与公司逻辑的不同理解,公司经营以及债权人保护的考量会以不同方式影响资金从公司到股东的逆向流出,进而影响实践中的交易结构与投融资的活跃程度。与域外类案的比较启发了对合同与公司的重新理解以及对市场逻辑的进一步回归。商事审判的这一转变又依赖、受制于职业经理人、市场中介、商事法官等要素的成熟以及专业、信用、声誉等品格的养成。这似乎是一个悲观的悖论:市场不成熟,商事审判便无法彻底贯彻市场逻辑;偏离市场逻辑的商事审判会进一步扭曲市场要素角色与功能的归位。“就公司治理和公司法而言,作为法律中的技术性规则,并不存在着所谓‘中国特色,的问题。”[74]于此,尝试采纳一种“渐进策略”[75]或许是可行的方案,以渗透公司的组织属性、董事的决策程序、市场中介的公司治理角色等观念,在合同效力与合同履行的区隔中使组织秩序与契约秩序相互嵌入。
第一,目前司法实践中与强制性规范关联的合同效力问题压倒性地作为核心甚至唯一争点的合同逻辑应予改变,实现合同效力与合同履行的区隔。公司因资本规制无法支付补偿或回购款不能导出合同的无效评价,在履行障碍的框架下,排除履行不能、不可抗力或情事变更,应定位为履行迟延,进而引致实际履行与损害赔偿的法效果。
第二,在合同有效的前提下,依托公司法机制,实现违约责任承担方式的灵活性与多元化。
可以基于公司的财务状况,延期或分期支付补偿或回购款。但补偿或回购款的支付期限和支付金额不能交由法官直接决定,而是由公司董事会以正当程序、依据公司聘用的市场中介给出的专业报告等作出商业判断,并由法官审查决策程序。此处,与商业判断规则不同的是,组织中的董事决策程序是通过法官命令启动的。
第三,不当的合同履行应在某些条件下面临债权人的直接挑战。例如,如果不当的支付决策给公司债权人造成现实的损害,在一定条件下,可认定董事违背对债权人的信义义务。[76]此处是债权人启动的事后救济措施,。
【注释】
[1]参见(美)美国风险投资协会:《美国风险投资示范合同》,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律师协会风险投资委员会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
[2]See Ronald J. Gilson, “Value Creation by Business Lawyers: Legal Skills and Asset Pricing”,94 Yale Law Journal, 262—264(1984).
[3]See Jeffrey Manns Robert Anderson IV, “The Merger Agreement Myth”,98 Cornell Law Review, 1183(2013).
[4]Gilson, supra note 2,p.264.
[5]See Victor P. Goldberg, “In Search of Best Efforts: Reinterpreting Bloor v. Falstaff”,44 Saint Louis University Law Journal, 1465—1485(2000).
[6]一项实证研究发现,在213个投资轮次中,有204个轮次使用了可转换优先股。See Steven N. Kaplan Per Stromberg, “Financial Contracting Theory Meets the Real World: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Venture Capital Contracts”,70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86(2003).
[7]参见陈友忠、刘曼红、廖俊霞:《中国创投20年》,中国发展出版社2011年版,第23、42、88页。
[8](2012)民提字第11号。
[9](2013)鲁商初字第18号。
[10]参见于晖:“‘甘肃世恒对赌案’后的一起‘逆转’裁决”,http://www.topcapital.com.en/pages/reportdata.asp?id=9937,最后访问日期:2014年8月22日;陈浮、张威:“最全面的对赌协议仲裁报告案例分析”,http://www.investbank.com.cn/Information/Detail.aspx? id=49143,最后访问日期:2014年8月22日。另可参见陈桂生等与北京安言信科投资有限公司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案(2015)二中民特字第00014号。
[11]参见彭冰:“‘对赌协议’第一案分析”《北京仲裁》2012年第3期,第188-199页;李睿鉴、陈若英:“对私募投资中‘对赌协议’的法经济学思考——兼评我国首例司法判决”,《广东商学院学报》2012年第6期,第82—90页。
[12]参见杨明宇:“私募股权投资中对赌协议性质与合法性探析——兼评海富投资案”,《证券市场导报》2014年第2期,第64—66页。
[13]参见傅穹:“对赌协议的法律构造与定性观察”,《政法论丛》2011年第6期,第68—70页;胡晓珂:“风险投资领域‘对赌协议’的可执行性研究”,《证券市场导报》2011年第9期,第68—73页;谢海霞:“对赌协议的法律性质探析”,《法学杂志》2010年第1期,第73—76页。
[14]参见季境:“私募股权投资中股权价格调整条款法律问题探究”,《法学杂志》2014年第4期,第49-55页。
[15]参见潘林‘对赌协议第一案’的法律经济学分析”,《法制与社会发展》2014年第4期,第171—178页。
[16]参见刘燕:“对赌协议与公司法资本管制:美国实践及其启示”,《环球法律评论》2016年第3期,第146-156页。
[17]参见张先中:“私募股权投资中估值调整机制研究——以我国《公司法》资本规制为视角”,《法学论坛》2013年第5期,第133—140页。
[18]SV Inv. Partners, LLC v. ThoughtWorks, Inc.,7 A.3d 973(Del. Ch.2010),aff’d, 37 A.3d 205(Del.2011).
[19]参见王利明:“我国案例指导制度若干问题研究”,《法学》2012年第1期,第79页。
[20]参见张骐:“论类似案件的判断”,《中外法学》2014年第2期,第530页。
[21]张骐:“再论类似案件的判断与指导性案例的使用——以当代中国法官对指导性案例的使用经验为契口”,《法制与社会发展》2015年第5期,第145页。
[22]参见刘燕:“重构‘禁止抽逃出资’规则的公司法理基础”,《中国法学》2015年第4期,第200页。
[23](德)K •茨威格特、(德)H •克茨:《比较法总论》,潘汉典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46页。
[24](意)罗道尔夫•萨科:《比较法导论》,费安玲等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74页。
[25]朱晓喆:“比较民法与判例研究的立场和使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第154页。
[26](美)莱纳•克拉克曼、(美)亨利•汉斯曼等:《公司法剖析:比较与功能的视角》(第2版),罗培新译,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1页。
[27]参见萨科,见前注[24],第74页。
[28]参见张文显:“部门法哲学引论——属性和方法”,《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年第5期,第11页。
[29]Mueller v. Kraeuter & Co.,25 A.2d 874(Ch.1942).
[30]See William W. Bratton Michael L. W?chter, “A Theory of Preferred Stock”,161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w Review, 1860(2013).
[31]See ibid.,at 1868—1869.
[32]通过Westlaw数据库检索,检索时间为2016年12月17日。
[33]See Leo E. Strine, Jr.,“Poor Pitiful or Potently Powerful Preferred”,161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w Review, 2030一2033(2013).
[34]Dodge v. Ford, 170 N.W.668(1919).
[35]Smith v. Van Gorkom, 488 A.2d 858(Del.1985).
[36]Basic Inc. v. Levinson, 485 U.S.224(1988).
[37]邓峰:《普通公司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5页。
[38]同上注,第36页。
[39]参见邓峰:“资本约束制度的进化和机制设计——以中美公司法的比较为核心”,《中国法学》2009年第1期,第99—105页。
[40]参见邓峰,见前注[37],第284—288页。
[41]参见环球律师事务所:“对赌在中国的司法实践研究报告”,http://www.globallawoffice.com.en/content/details_40_848.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6年12月29日。
[42]北京匡富投资有限公司等与中国风险投资有限公司等合同纠纷上诉案(2014)二中民终字第04990号0
[43]孔凡鹏与林卓彬民间借贷纠纷案(2014)深中法民终字第2122号。
[44]。在案件历经不同审级,其裁判理由、裁判结论有出人的情况下,本文只统计终审判决。
[45]翁吉义与胡书来等股权转让纠纷案(2013)沪一中民四(商)终字第1096号。
[46]只存在一个例外,在陈桂生等与北京安言信科投资有限公司仲裁裁决申请案(2015)二中民特字第00014号中,。尽管当事人基于“对赌协议第一案”中最高法的判决,质疑仲裁庭认定“对赌协议”有效的结论,,而是认为仲裁庭对案件实体处理的问题不属于应撤销仲裁裁决的情形。
[47]有两则案例涉及中外合资经营企业股权转让或者国有资产交易须经审批的强制性规定,相应的效力形态是“未生效”。参见国华实业有限公司与西安向阳航天工业总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上诉案(2013)苏商外终字第0034号、南京诚行创富投资企业与江苏省盐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纠纷案(2016)最高法民申410号。
[48]孙宪忠:《中国物权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276页。
[49]同上注,第279页。
[50]参见蔡立东:“行政审批与权利转让合同的效力”,《中国法学》2013年第1期,第62页。
[51]参见韩世远:《履行障碍法的体系》,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62—81页。
[52]参见首都信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诉北京亿思瑞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等股权转让合同纠纷案(2009)海民初字第26101号、上海立鸿投资合伙企业诉浙江中宙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等股权转让纠纷案(2014)沪一中民四(商)终字第1334号。
[53]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五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50页。
[54]参见许德风:“组织规则的本质与界限——以成员合同与商事组织的关系为重点”,《法学研究》2011年第3期,第96—97页。
[55]See William T. Allen, “Our Schizophrenie Conception of the Business Corporation”,14 Cardozo Law Review, 264—272(1993).
[56]邓峰:《代议制的公司——中国公司治理中的权力和责任》,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7页。
[57]同上注,第168页。
[58]邓峰,见前注[56],第42、55、180页;参见罗培新:“股东会与董事会权力构造论:以合同为进路的分析”,2016年第2期,第122页。
[59]参见刘燕,见前注[22],第194—196页。
[60]。
[61]See Stephen M. Bainbridge, “Director Primacy: The Means and End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97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Law Review ,605(2003).
[62]See Lynn A. Stout, “The Toxic Side Effects of Shareholder Primacy”,161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w Review, 2013(2013).
[63]参见莱纳等,见前注[26],第2页。
[64]Edward B. Rock, “Adapting to the New Shareholder—Centric Reality”,161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w Review, 1910(2013).
[65]See Stout, supra note 62, pp.2003—2019.
[66]See Margaret M. Blair & Lynn A. Stout, “A Team Production Theory of Corporate Law”,85 Virginia Law Review , 247—328 (1999).
[67]朱慈蕴、沈朝晖:“类别股与中国公司法的演进”,《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9期,第156—157页。
[68]See Bratton W?chter, supra note 30,p.1886.
[69]法律顾问是 Freeborn Peters LLP,财务顾问是Alix Partners LLC。
[70](美)约翰• C •科菲:《看门人机制:市场中介与公司治理》,黄辉、王长河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页。
[71]同上注。
[72]参见郭力方:“PE‘君子协定’期待阳光化”,载《中国证券报》2012年5月14日,第A15版;张志浩:“为‘对赌’条款正名”,载《上海证券报》2012年5月17日,第F06版;刘志月:“‘对赌协议’纠纷日趋多样需重视”,载《法制日报》2015年4月18日,第8版。
[73]例如强静延与曹务波、山东瀚霖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2015年12月裁定再审,(2015)民申字第3227号。
[74]邓峰,见前注[56],第74页。
[75]周其仁:《改革的逻辑》,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第282—283页。
[76]我国公司法目前尚不存在董事对债权人负有信义义务的相关规定。发源于美国的这一制度已被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德国等国家的公司法引入。这一义务的发生有其严格的前提条件,即公司丧失偿付能力。参见朱圆:“论美国公司法中董事对债权人的信义义务”,《法学》2011年第10期,第129—137页。
原载于《中外法学》2017年第1期
长按二维码可轻松关注;转载须附二维码。
雅俗共赏 以俗为先
补漏客(Bloke)
相关推荐
友情链接
Copyright © 2023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北京物流信息联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