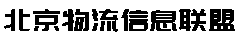
2022-03-24 06:18:00
『时光捡漏』您生活的日记本
【配图均来自网络】
点击下面蓝色字体,欣赏上期精彩文字
文 | 鲁 旭
09
事情复杂了。
按照上边的安排,工作组这几天的主要任务是清查财务。我把工作组的人分成几个小组,小赵、小刘、小谢他们三个年轻人由老张领着,都在清查村委会和各村民小组的财务,只有我和小陈在为下一阶段工作做准备,提前进入到了村级领导班子整顿中来。我和小陈商量了一下,决定趁热打铁,就目前掌握的情况给他来个穷追不舍。
我们又找了村委会副主任李拴成。老李是个爽快人。我们刚坐下,还没说明来意,他就说:“是来了解村班子的吧?这事我可不好说。”
“你怎么知道我们是来了解班子情况的?”我正为他判断的准确性吃惊,小陈已经接过了话题。
“那还用猜?就我们村的情况,不论谁来了,只要你是真正想把村子搞好,就必须解决村委班子的问题。而要解决这个问题,都必须找我了解情况。”
我和小陈对望了一下,小陈却没有再开口,他没有理解我的意图。
“这次你猜错了。”我怕又走了前几次乡上下派干部的老路,想换个方式,没有追问为什么非得找他了解情况。“我们这次来找你,是想了解咱们村对群众脱贫致富的打算。”
李拴成好像松了一口气:“村上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打算。给上边汇报的那些措施啊,办法啊,都是虚的。说实在的,支书和村长尿不到一个壶里,可就难为了我们这些跑腿的,也苦了全村群众。”
我在心里承认老李的话有道理。虽然我没当过领导,可我知道,一个单位里正职和副职如果意见完全相左,工作是一定会受影响的。
“怎么就难为了你们,又苦了群众?”小陈明知故问。老李没有就回答,他盯着小陈看了半晌,反问小陈:“你参加工作多久了?”
这一下来得突然,一晌口齿伶利的小陈一时弄不明白他发问的目的,望着我不知该不该回答。我笑着说:“他是大学生,毕业时间不长,才工作了四五年。”老李笑了,说:“怪道来!这么说吧,要是在你们单位里,局长叫你写材料,副局长叫你去下乡,两人说的话都没有商量的余地,你觉着难为不难为?”
“没这么严重吧。”
“我这只是个比方。就说我们村吧,当干部的都想把村上搞好,可各人有各人的干法,就是统一不起来,到头来什么事也做不出个决议。我是村上的老人手了,经过了几届班子,每逢这种时候,我就觉着自己特别没有本事。说实在话,要不是你们来了,我怕给你们添麻烦,我早就不干了!”
“那你就没有主意?”小陈问。
“什么主意?”
“村上的经济发展呀。”
“不用我出主意,村上讨论过的方案就挺好。”
我和小陈都摸不清他说的方案指的是什么,老李又不往下说,我只好试探着问道:“你说的是有关汪富承包果园的方案吧。”
老李点了点头。
“据我们了解,村上就这件事并没有做出决定。你是同意支书的意见,还是同意村主任的意见?”
“汪有才能有个啥意见!他要不搅和,村上早做出决定了!”
看来,李拴成是支持宫民主的方案的。
“汪村长对宫支书有意见?”小陈问。
“我也说不准。要说有意见吧,汪有才当村委主任是宫民主提的名,两人关系也挺好;要说没意见吧,宫民主提出想干什么,汪有才总有理由让他干不成。两三年了,两人就这么僵着,村上也就这么耗着。唉!”老李重重地叹了口气。
这一声叹息令我感到了压力。不知怎么搞的,我突然想起了我那两位老同事的话。他们一个是乡党委书记,一个是曾经处理过这件事的老人手,是过来人。我不知道应该怎么理解他们的话,思想就抛了锚,再也回不到李拴成跟前,谈话也就进行不下去。
我提出要走,李拴成也就起身送我们。出了屋子,小陈突然捅了我一下,我一怔,这才想起还有一件大事没有问。我正思谋如何把话题引回来,小陈却开了口:“老李,你这院子都够上农展馆了!”
我抬头打量李拴成家的院子,他住的还是一边盖的老房,我发现院墙上,屋壁上,屋檐下,还有院子里的树上,到处挂的是玉米棒子和辣椒串。金黄色的玉米棒子配上火红的辣椒串儿,颜色是那么艳丽和谐,用“鲜艳夺目”来形容绝不过分!可我心里有事,也没弄明白小陈把话题引到庄稼上的用意,只好随声附和道:“就是!人说秋季是农村最美的季节,你的家怕是农村最美的了。”
“哎老李,能不能把我们领到你的承包地里看一看,让我们也享受一下田园风光?”小陈突然话锋一转。
我突然明白了小陈的想法,不由佩服起他来:年轻人脑筋灵活,什么事都可以想出办法来。而我,就只能凭着经验,按照正常步骤,顺着一条思路往下想,从来就不会“别开生面。”前一阵子传闻小陈要提升,我还有点嫉妒,现在看来领导要是提拔我而不提拔他,那就是大错特错了!
秋季的田野到处显现着成熟,田坎上的草是墨绿色的,崖畔上的野菊花是金黄色的,而刚垦开的土地是深褐色的,堆在田边的秸秆已经成了黛色,就是天空的色彩,成是那种高深莫测的蓝色,崖顶上几只洁白的山羊,更衬出大自然色彩的深奥。
“老李,听说你们村过去有个实验农场,现在还在么?”我正陶醉在大自然的美妙色彩中,小陈却开始工作了。我开始佩服起这个年轻人来。
“那都是多少年前的事了,农场早散了。”
很好!小陈这种探旧搜奇式的问话并没有引起老李的警惕。
“可惜!要是农场还在,我还想在里边搞点试验哩。”
“你又没有当过农民,能种个啥?”
“种花!你不知道,现在种花可赚钱了,城市里对花的用量很大。”
“这倒是个新想法。”老李被小陈说服了。
“农场的地还在么?”
“都承包给私人了。”
“都包给谁了?”
“你问这干啥?”
“是工作,也是为我自己。”小陈纯真地笑着说。
这时候,老李才明白自己被眼前的年轻人给套住了。他是个痛快人,略略想了一下,就把村农场土地承包的情况说了出来。“村农场一共三十亩地,八个村民小组的组长每人承包了一亩,五个村干部每人承包四亩,给支书和主任各加了一亩。民主不要,他的那份儿就由有才包去了。”
“这件事,是你们开会定的?”我问。
“是村委扩大会定的,当时各组组长都参加了会。当时考虑县乡干部下来工作,几乎每次来都要在村上吃午饭,村组干部都有接待任务。把村农场的土地承包给他们,就不再发给他们接待补助费了。对了,当时开会宫书记没来,他只让组长给捎了个话,表明了一下他的态度。”
“什么态度?”小陈问。
“就是他不想承包那地,因为他有自己的事要干,地多了顾不过来。”
“他有什么事?”
“他在家开了个修理厂。”
“骗人!修理厂起码得有几件设备,我去过他家,只见他家有几间空房,根本就没见他有什么设备!”小陈沉不住气了。其实这也是我的想法。宫民主不愿承包村农场的地一定另有想法,说他顾不过来只是托词而已。
“他没有骗人。他是有设备的,而且还相当全呢。”
“设备在哪里?”
“在村饲料厂的修理车间里。”
10
工作组住的是民舍。我住的这一家的主人到外地打工去了,我实际上一个人住了一座院子,从厨、卫到花园,应有尽有,我自己对别人吹嘘说我住的档次不比别墅低。只是屋子里只有一张木板床和一张三斗桌子,铺盖都是自己带的。因为我是组长,我的住处有时要当作工作组的会议室用,村上给借了几把椅子和几个小马扎。这儿没有电视,没有收音机,报纸也要晚来几天。吃过晚饭,我正思谋在哪儿消磨这漫漫长夜,工作组的老张披着件黄军大衣推门进来了。他这人爱笑,一进门就笑着说:“今晚没啥要紧事吧?”
“没有。”
“那就好,咱们可以放开谝。”
“完全可以。只是我这儿没有酒,晚茶我又不能喝,一喝就睡不着觉。给你来一杯吧?”
“我自己来!你那算啥茶叶,一点味儿都没有。茶叶、熬茶的家伙咱都带着哩!”说着,他变戏法似的东一摸西一摸,烟、酒、茶叶就都有了。令我吃惊的是竟掏出了一个还没有巴掌大的电炉子,一个还没有茶杯粗的黑沙罐儿!他一边掏一边说:“长期在乡下蹲着,吃的百家饭,饥饱咸淡不说,光是卫生条件、水色软硬就够你适应的。我这人不行,是个粗人,可这狗日的肚子还娇气的不行。你要不喝点酽茶它就给你闹腾,还就是受不了!”
老张一边说话一边收拾。他把酒推给我,为自己熬了一罐儿浓得像汤药一样的茶,像喝酒一样细细地品着开始闲聊。
老张突然来访,我下意识感觉到他是有事要说,谁知他尽说些不着边际的笑话。他比我长五六岁,时不时以过来人的口吻给我讲些在农村工作的经验。茶喝过两蒇,酒饮过三钟,他突然问我:“你打听过村上农场土地的承包人了?”
“我和小陈调查过。怎么,有什么不对吗?”
老张的问话以及语气、措词都令我不快。这是什么语气啊?简直是在审问!怎么能用这样的措词跟领导说话啊?好像他面对的不是工作组的组长,而是一个爱打听小道消息的小人!要是在以前,说不准我也会这样问。可现在我是领导,是组织上派来独当一面的工作组组长!代表着一级组织!但我知道自己没有把这种不快表现在脸上。我发现我也变得深沉起来了。
“能有什么不对?你是工作组组长,有权决定干什么不干什么。”
阿弥陀佛,多亏你还记着我是工作组组长!要不然还不知道会说出什么来呢!我在心里这样说。
“群众对这事有议论了。,并没有在乎我表情的变化。我想我的表情肯定有变化,毕竟我是初出道的“领导”呀!
“这个事在乡镇是明摆着的事,各村都有,也就是你们说的‘普遍问题’,群众也已经认可了。”
“群众认可了?”
“群众认可了。要不你查一查这次搜集到的意见,看群众对这一方面有没有反映。”老张说得有理有据。
直到这时,我才发现群众反映的问题虽然不少,却确实没有针对村农场土地承包这方面的意见。
“你们说的是农场土地承包的事吧?,小陈突然推门走了进来,“不能因为这个问题普遍存在就听之任之。我看只要有问题,越是普遍存在的问题越应该管。”
小陈到底是年轻人,进屋还没落座,意见已经发表了一大堆。可奇怪的是小陈一进屋,老张立即起身招呼,又是让座又是熬茶,忙得不亦乐乎。让我这个队长兼房主相形见绌,自愧不如。他人忙着,嘴也没有闲着,而且言词热烈,谈吐风趣,可就是不接小陈的话茬儿。
小陈是何等聪明的人!,就知道老张不乐意他在这时候进来,也就是不想跟他讨论这个问题。他不再强调刚才的观点,一边推脱说自己晚上不能喝茶,一边一本正经地对我说:“组长,我是来提建议的。我刚才到清财组住的地方去了一会儿,他们的工作已经基本结束,都想着要休两天假。我们到风庄来已经两个星期了,也应该让同志们休息一下,安排一下家里的事情,再跟原单位勾通一下。”
得到我肯定的答复,小陈乐呵呵地往外走,老张和我一直把小陈送出院子。在回屋里时,:“到底是年轻人,‘初生牛犊不怕虎’啊!”以当时的环境和氛围,,也就没有接他的话茬儿。
回到屋里,,也没有了小陈来之前的热情。我多方启发,他才告诉我他刚才说那些话,其实是从乡政府里听来的。说过了,还一再嘱咐我不要受那些意见的干扰,该咋干还咋干。临走了,又以不经意的口气重复了一句他已经说过的话:“初生牛犊不怕虎”啊!
这一次我糊涂了:他这是说小陈呢,还是在说我?
我又想起了在乡上干事的两位同事,同时也就想起了他们说过的截然相反的话。
这一夜我失眠了。
11
工作组休了两天假。这是宣告工作组工作进展顺利,也是宣告我们的工作告一段落,就要进入下一阶段的工作。
这两天假我休得特别忙,只有吃饭和过夜时才能在自己家里,其余时间全忙活在其他人的家里了。虽然是临时工作,怎么说也是离开原单位了,本单位的领导你总得见一下吧!还有那些平时说得来的哥儿们,你也得和他们谝上几句。单位在休假,你要见他们,就只有追到家里去。
说来也怪,在单位上班时,这些人全不把我放在心上。可才离开两个星期,我的事竟成了他们谈论的中心。首先是领导,他一见我便说:“听说你干得不错呀!”
“您听谁说的?”我弄不明白他这是顺口说一句客气话,还是真有什么事传到了他的耳朵里,就紧着问了一句。
“这你就别管了。我听说你这几天在淘乡上的老茅子(陈年厕所)。”我正想说我没有淘乡上的茅子,还没等开口领导抬手制止了我。“我没有要干预你工作的意思,你现在大小也是个领导,有权决定干什么,怎么干。我只是想提醒你,你还年轻,在领导岗位上也没干过,现在独当一面,对那些比较敏感的事情可要小心,别弄得到时候撤不回来,让我们去营救。”
说了这句话,他便不再提我下乡的事,只管问我生活习惯不习惯,还打听有关油菜叶面的事,有说有笑。可我已经高兴不起来,也笑不出来。坐了一会儿,我就告辞出来。
见了几个哥儿们,他们一下子也都成了消息灵通人士。我本想利用休假换个环境,让一直兴奋的大脑休息一下。可我发现,无论走到哪儿都躲不开自己的工作,就是在家里也要受老婆盘问。于是,第二天吃过中午饭我就返回了风庄。我知道这会儿工作组的其他同志还没有来,我可以在这里好好休息一下,也可以为下一阶段工作打个腹稿。
从乡上到风庄要走五六里路。我已经没有汽车可坐,早已沦为吃汽车屁一族,这一段路只好开动两条腿走。好在我正有许多心事要想,就权当是散步,反正没有熟人看见。我不知道我们应该怎样进入下一阶段,因为按我的想法,上一阶段的工作实际上只开了个头儿,还没有搞出眉目来。有了在城里听到的那些反响,我不知道下一阶段工作应该怎么去搞!
村子里好静,我只见到几个半大孩子,他们也在休星期假。我开锁进门,连身上的土都没有扑打一上就把自己扔到了床上。两天了,我总算找到了一个只属于我的安静环境。
我正在暗自庆幸回来得正确,宫民主却突然出现在我的卧室兼办公室门口。
说他突然出现,是因为在此之前他只在我刚来那天晚上来过一次,我根本就没想到他会来。可他来了,还是那付一切都无所谓的样子。他一边大声打着招呼,一边把手伸给我。我留神了一下,他的手已经洗过,虽说还沾着油污,已经不会再传染到我的手上。于是我拉着他的手,把他迎进了我的屋子。
“你怎么这时候来找我?不知道我们在休假吗?”我笑着问宫民主。
“我知道你在家里坐不住,会老早就来。”
“那也不止于我刚到门口你就在这里等着呀?别是给我放了哨吧!”
“我还真给你安排了个侦察兵。看,就是他。”他指着站在院里的一个孩子。“你一进村他就向我报告了。”
我认识那孩子,是对门李拴狗家的,就招呼他进来。他好像没听到我的话,连窝也没挪一下,依然在门边向里张望。我看那孩子也就十岁左右,一脸顽皮相,不是那种听话的好孩子,就说:“他会听你的?”
宫民主没有正面回答我,只对那孩子说:“去,告诉你们那帮家伙,离这里远一点,别让人打扰,我们要说正事。”那孩子也不回答,扭身就跑走了。果然,整个下午没有人再来找过我。
我更佩服宫民主了。一个人让成人听话是比较容易的,因为成人懂得韬晦之术,心里的不快可以不表现出来,。可孩子不同,他们心如明镜,不染尘埃,哪怕你是他的家长,也很难让他做他不愿意做的事。有时候他还会逆着你的话来:你不让他做的他偏要做,你让他做的他偏不去做。可这个一脸顽皮的孩子竟让宫民主“派”走了,这不能叫我不服。
到了我的屋子里,我正要取烟,宫民主拦住了,说:“抽我的吧。你就那点儿工资,再要用烟招待人,就没有给老婆交饭钱的了。”我听他这么说,也就没有坚持。接过他递过来的烟,正想给他泡杯茶,却发现水壶是空的。我正尴尬,房东大婶提着一壶开水来了。
“你怎么知道我回来了?”
“二娃说的。”
我想起来了,二娃就是刚才盯着我的那个孩子。我发现我钻进了一个套子:这一切都是宫民主安排好了的,包括我回家以后的事,好像都在他的掌握之中。
宫民主找我好像没有什么大事,正如他说的,是来陪我说说闲话。他随便拣了个话题说开,东一句西一句,从天上到地下,从国内到国际,从总统下台到生活琐事,无所不谈,就是不说本村的事。他虽然说话语速比较慢,但说起来头头是道,逻辑严密,并不是我想的那种木呐人。我看他谈锋正健,几次想打断他的话题,又觉着这么做有点赶客人走的意思,就手下留情口边积德,没有开得了口。直到该吃晚饭了,他才说出他想到内蒙去一次,得请几天假,还要我派个人陪着。我问他去干什么,他说去考察一下那儿的饲草市场。如果有可能,他想为村上的饲料厂订一份合同,给内蒙加工饲草。
“别又是给秸秆打主意吧。”我想起他办饲料加工厂的初衷,就开玩笑说。
他笑了,“就是为了这事。你也看到了,咱们的饲料厂用不了多少秸秆,绝大多数都丢在地里。”
这是实情,也是好事,可我拿不了主意。我一本正经地说:“事情是好事情,可村支书要离开,我却没有权批,得报乡政府和驻乡工作队批。马上就要开始村班子整顿了,我估计报上去也批不下来。”
“我这个念头已经起得晚了点,早玉米已经收完了。如果再拖几天,晚玉米一开始收割,就只能等明年了。”
我无话可说、这时候,我突然感觉我的官太小了。
“整顿安排了几天?”过了一会儿,宫民主突然问。
“两个星期。”
“你打算怎么搞?噢,我只问方法。”
我笑了。宫民主看似实在,其实人很精明,他怕背上打听人事安排的嫌疑。
“我还没来得及和你商量。我想先学习文件,提高认识;再组织讨论,分析班子存在的问题;第三步决定人事安排。”
“行!”他想了一下又说:“估计这会儿小陈已经来了,你给他谈一下,我们今晚就出发,坐晚上的火车,明天就可以到内蒙。那里我有朋友,找他帮忙,两三天就可心把事办完,五天内我们就能赶回来。你就不要向乡上汇报了,就假装不知道这件事。你不汇报,乡上不会有人来查。至于小陈,你不说就更没有人查。”
“要去你去,小陈不能去!”我说的非常坚决。我这领导还没当实在呢,小陈也还要考虑进步,不能因为这点小事坏了我和小陈的前途。
“行!那我带个村委。”
“这是你的事,你看着办吧。”这人太武断,我有点不高兴,刚刚对宫民主产生的好感烟消云散了。
12
整顿村级班子工作正式开始了。乡上只是不断地安排工作,督促我们及时汇报进展情况,并没有检查村班子的成员齐不齐。一切都和宫民主的预言一样,我的担心成了多余。
放下了这件事,我就又想开了宫民主:也不知他把事情办成了没有?这是在基层组织整顿期间,按照常规,应该是工作组在主持村上的工作。如果宫民主在这时把为内蒙加工饲草的事情办成了,也就算我这个工作组为风庄村人民办了件大好事。工作组受表彰那是一定的了,说不定还会在全县造成一定的影响。要真是这样,我也就成了名人,当领导的事也就包进了包袱。于是我就在心里企昐他把事办成。于是就后悔没有让小陈和宫民主一同去。说实话,如果不是怕挨批评,我也想跟着他一起去见识见识外边的世界。
在我眼巴巴地企昐中,宫民主回来了。他进我屋门的同时,乡上的干事老李也进了门,两人就像约好了一样。我和他们打过招呼,先问老李有何贵干。他虽然是我的老同学,可毕竟代表着一级组织。老李也不避人,开门见山说他是乡工作队派来调查整顿期间宫民主离村这件事的。说完还有意看了宫民主一眼。
“这事与工作组无关。我是村支部书记,什么时候想干什么事情,自己还能拿了自己的主意。”宫民主的话充满着火药味。
“不!这件事我知道……”我还想说得更有力一点,老李摇手止住我:“你们先不要急着争。民主,你先说说事情办成了没有。”
宫民主没有急着说,而是先望着我。我看了看老李似笑非笑的样子,突然记起老李对风庄村领导班子的看法,就对宫民主说:“说吧,说不定老李还能给咱参谋参谋。”
“别这么说!”老李还是那付样子,“我可是钦差大臣,是来了解情况的。想知道民主这次出去的结果,只是我的好奇心,你们千万别往别处想。”
宫民主比我更了解老李的性格,见他往清里洗自己,就笑着说:“嫑洗了,你那是猫娃洗脸,根本就不管有没有水,也不管手上是不是干净。再洗下去,只能越描越黑。再说,你李瑜到了我们风庄,吃啥饭都是油菜叶子面条,站啥立场都会是一身黑不溜秋,还是坐下听我给你卖牌。”
宫民主这招还真管用,老李真的坐下了,脸上的表情也认真起来。于是,宫民主便从一路的见闻说起,直说到和内蒙几个饲草供应商谈判的情况。正说着,他老婆端着一碗干面进来了,我们这才知道他还没有吃饭。我一边自责,一边给民主倒了一杯开水。宫民主也就一边喝开水,一边就着大蒜吃起干面。一边吃,一边还在说着谈判的情况。
宫民主他们的谈判不能算成功,也不能算失败。因为他们去得晚了,当地需要的饲草已经有了安排。再加上以前没有相似经历,双方没有打过交道,各自对对方的情况不了解,也就是没有信誉度。蒙古那边虽然觉着这是好事,可不敢下过大的注。而咱们这边,因为对牧畜饲草的要求知之甚少,也不敢提供过高的保证,因而谈判很难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他们跑了几家饲草供应商,大致都是这个意见。还是他的蒙古朋友从中说合,才签了份先供应样品进行试销售的协议。
“成!你这家伙还是心眼多!”还没等我说话,老李抢先开了腔。“这样的结果已经很不错了,只要你们把样品弄好,让人家满意,这生意就算成了。”
“就是!你要是把这件事办成了,就等于给全县人民办了一件好事。”我说。
“别说得那么好听,我是村支书,我只知道我们村里的事。”宫民主笑笑说。
“花钱多不多?你可别认为这是出公差,拿着村民的血汗钱去开洋荤,一分不值二分地乱花!”老李一本正经地说。
“钱花多花少是我的事,你管不着。”宫民主一脸油滑。
“我怎么管不着?别忘了,我还是风庄的包村干部,风庄的事我就得管!”老李突然激动起来。
“看把你能的!我在走内蒙以前就已经想好了,反正我是第一次到内蒙古,这次的钱全由我出,就算咱也外出旅游了一次。”
“这怎么行?你这是因公出差!”我终于找到了说话的机会。
宫民主显然对我的话不感兴趣,只是对着我淡淡地一笑,转而对老李说:“说吧,钦差大臣,我的问题你打算怎么处理?”
“这倒还有点难度。”老李也转过了话题。显然,他已经默许了让宫民主自己负担这次出差的费用。“你呀,就那样子了,死猪不怕开水烫。可我这老同学就不一样。他干了十几年了,好不容易捞着一次当官的机会,总不能因为你影响他的官声吧!”
“就是。你是乡上有名的诸葛亮,给咱好好转通一下。”宫民主说得相当认真。我正想开口表白自己,,伸出大手往下一压,硬是把我的话给压回去了。
“说你是私自外出吧,会影响我这老同学的名誉,让人觉着他这个工作组的组长就是管不住你。还有,上边要是觉着你办的事是好事,这功劳也就没了我这老同学的份儿。可要说你们是商量好了的,又显得我这老同学刚当个临时官就跟领导对着干,明显地抗旨不遵。工作队明文规定整改期间村干部不能外出,他放你走,就是明知故犯。”
“别分析了!说吧,你让我怎么说?”宫民主喜欢直来直去。
“你们俩先不要急着向上边汇报,听我的消息。我回去试探一下领导的态度,如果他认为这是好事,我就说你们是商量好了的;如果他发了雷霆之怒,就只好委屈民主了,说你没有告诉工作组,是偷着出去的。反正你不听招呼已经是门缝吹喇叭鸣声在外了,只能算是已经断了气的猪,多烫一次少烫一次关系不大。”
老李一再拿猪来形容宫民主,明显有戏噱的成分,我都听得有点刺耳,宫民主却并不在意,仍然有说有笑。三个人说来说去,只有同意老李的意见,先这么试一下。总之,不能让工作组的正常工作受影响。
事情虽然这么定下来了,可我心里却犯了叽咕:这宫民主才回到家,乡上的领导咋就知道得这么快?这事就我俩和小陈知道,是谁走漏了风声?这些话只是在我心里翻腾,我却没有胆量拿出来问李瑜。
又说了会儿闲话,老李要走,宫民主却笑着说:“咋,不去看看你的相好吗?”
宫民主这话一出,我立即头皮发炸!作为一个干部,这是何等敏感的问题!我一时竟不知说什么好。老李虽被宫民主揭了疮疤,却是依然故我,脸上不绿不红,以非常正常的口吻说:“今天怕是去不成了。乡上还在等我的消息,我已经来了半天,也该回去汇报了。”
和李瑜有相好这件事相比,宫民主出外走漏风声的事就轻多了,我的心情稍微有了些好转。
13
我这看似老实的老同学在风庄村有相好,似乎是公开的秘密,而且他自己也是一付满不在乎的样子,竟然当众供认不讳,这一点令我百思不得其解。我决心弄个水落石出。
老李是我小学时的同学。能在一起上小学,当然住的不远。我略施小计,就把他家的情况打听了个一清二楚。他的小名叫狗娃,大名叫李瑜。李瑜弟兄两人,他是老二。兄长在外地工作,已经在外地成了家。他的父母都还健在,七十左右的人了,都还能下地干活。李瑜的妻子是位农村妇女,干活利落,也很贤惠。他们有一对儿女,都在上初中。他是乡上的一般干事,一月的收入也就三百多块。好在哥哥的收入比他高出三四倍,嫂子也不是那种斤斤计较的女人,父母的生活费便全由哥哥承包了,每月都会按时把钱寄回来。当然,这钱如果父母花不了,就全部落入李瑜的腰包。因而,在收入水平普遍不高的情况下,他就算提前进入了小康生活。
也许,正是这提前进入小康的生活,使他也提前进入“饱暖思淫欲”的不良阶段,在外养起相好来了?啊呀我的老同学,看来你的思想还是有问题的!要不,你都在乡镇干了十几年了,凭你“诸葛亮”的能力同,怎么还是个老干事,就是提拔不起来呢!
不行,我得把这件事弄清楚!不说为了组织,起码也得对得起老同学这个称呼!
第二天上午开完会我没有去吃派饭,而是拉住村委会主任汪有才,硬是要到他家里去吃饭。我把村上的干部分析了一下,汪有才属于那种夹不住话的水嘴,你要向他打听事情,只要他知道点缨缨,就会说出个萝卜来。
这次来他家吃饭是突然袭击,汪有才没有来得及准备七碟子八碗,但那临时凑起来的饭菜也还是有质有量,说实话,比我回家休假老婆特意给我做的强多了。可我的心思不在饭菜上,未等开吃,我就开说了。
“听说我那老同学在你们村有个相好?”
“你那老同学是谁呀?”汪有才这是明知故问,我从他的眼神里已经看出来了。
“李狗娃。”我故意说了老李的小名。
“李狗娃是谁?”汪有才这回是真的不知道了。
我笑了。你可以耍我,我也可以耍你!他李瑜可以有相好,我也就能把你的小名告诉给受他管辖的人!“李狗娃就是李瑜。”
我原以为汪有才听了李瑜的小名会哈哈大笑,谁知汪有才不但没有笑,反而一脸严肃地对我说:“老刘,你不该这么说老李,他可是个好人。”
“他是好人?”这回轮到我吃惊了!
“他是个好人。说实在的,在乡干部中,能得到我尊敬的人不多。可老李就是这不多的人中最好的一个!”
这一回我真的坠入了五里雾中。“好人还能在外有相好?”说了这句底气不足的话,我自己也觉着有点强词夺理。
“这你就误解了。”汪有才笑了。他把筷子递给我,说:“你来就是为这事吧?来,咱们一边吃一边说,别让饭凉了。”
就着有才老婆做的面条,汪有才给我讲了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
“这事情已经好几年了,要真个是件风流韵事,早就传到你们城里人的耳朵里去了。可这偏偏就是件实在事,没有传播的价值,你至今还在当新闻听哩。”
汪有才吃了口面,望着我笑着。我感觉到那笑容中有种优越感,还有点对我的嘲弄,好像我就是那种爱传播小道消息的小人。我没在乎,听他继续说下去。汪有才一开口,我才发现他是个讲故事的天才,那时间,那场景都组织得很好,还能引人入胜呐!
“那是在87年的初冬,一天下午,老李奉命到魏庄村去办事。那一天下着小雨。你知道87年秋上就没有好好下过雨,久旱的土路被雨水浸泡得就像发面团,脚一踏上去就会带起一个大泥坨来,别说摩托车,就是自行车也骑不成,老李是开着他的‘11号’去的。咱们这里有句老话:‘十月天,碗里转,赖婆娘只做两顿饭’。老李本来就去的晚了,等和村干部说完事,时间虽不是很晚,可天已经快黑了。雨还在不紧不慢地下着,这是那一年的最后一场雨,要是能坚持下到第二天,这雨就该变成雪了。初冬的风虽然还够不上刺骨,可和着冰冷的细雨打到人身上,一样冷得人瑟瑟直抖。天越来越黑,路上已经没有了行人,老李穿着雨衣只管盯着脚下往前走。当走到距我们村不远的支渠边,散堆在路边的玉米秆儿突然哗啦响了一下,老李被吓了一跳!为了给自己壮胆,他大声吆喝:‘谁!出来!’
“那玉米杆丛又动了一下,慢慢地钻出一个孩子来。老李低下头一看,是个七八岁的女娃儿。她头发乱蓬蓬的,身上的衣服撕开了几个口子。天色太暗,老李看不清她的脸色和表情,她怕孩子遇到什么不测,就又问:‘里边还有人没有?’
“那孩子嗫嚅了半天才说:‘没有’。老李以为是孩子惹大人生气被赶出来了,就问她是谁家的孩子,那家伙低下头不再回答。那天实在太冷,老李冻得不行,打算尽快解决问题,就问她是那个村的。那女娃显然怕被送回家。她不再回答老李的问话,两腿慢慢地挪动着打算再次钻进玉米秆丛里去。
“老李发现了孩子的企图,伸手抓住了她。这一抓之下,他才发现这大冷的天气,孩子竟然只穿着一件露体的单衣!她那童稚的身体已经冰冷如铁了!他急忙脱下雨衣给孩子披上,也不管孩子是否愿意,强行抱起孩子到了我们村。我是离路最近的村干部,他脚一顺就进了我的家。
“老李进门时我刚好在院子里,见他怀里用雨衣包着个东西,也看不出是个啥,就笑着说:‘你来了就行了,还带礼物做啥。’他话也不说,只顾往屋里走,说:‘快找件衣服,要孩子的。’到了屋子里,他把孩子放下来,我才看清他抱的是瞎老二家的女子。”
“瞎老二?”
“这人你不认识,已经死了好几年了。”
“他家里还有什么人?”
“瞎老二是个逛三,打孩子时父母就死了,他一个人就靠着生产队瞎逛。土地承包以后他逛不动了,就到处偷人,三十多岁还没娶上媳妇。后来他本家叔叔到外地做生意,给领回来一个姑娘,两人就结了婚。谁知那姑娘有精神病的底子,开始还好着,可瞎老二恶习不改,又去偷人,派出所到家里来抓人,瞎老二被带走了,媳妇却吓得犯了病。生下这孩子的那一年,瞎老二和人打群架被打死了,这媳妇的病就再也没有好,而且一天比一天重。这女娃还是靠了左邻右舍帮助才长到这么大。也许是命吧,这女娃懂事特别早,两三岁时就知道照顾她妈。那女人病的时候也很疼孩子,可要是病犯了,就不要命的打孩子。每到这时候,要是有邻居看见了,就把孩子领去照顾两天,等那女人的病好一点再送回来。如果没人碰上,这孩子就只能自己跑出来。”
“这孩子上学了没有?”我问。
汪村长笑了:“你们到底是老同学,老李当时也问了这个问题。孩子长到六岁,村上就给报名上学了,一切学费杂费全由村上掏。可那女人一犯病,孩子的吃饭就成了问题,因而常常旷课,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老师都不愿意带。村上为这事还专门开了会,决定由几个村干部轮流给孩子管饭,一家十天。可那女人的病一轻,就到处找孩子,还对收留孩子的人家漫骂,后来也就没有人愿意再管了。”
“哪后来呢?”
“老李知道了这女娃的身世,当晚就住在了我家。第二天,他特意去看了瞎老二的媳妇,见她的病看好的希望不大,没说什么就回了乡上。过了两天,他带着老婆来了,给这母女俩送来了衣服和吃的。最后通过村委会,把这女娃接到了自己家里。”
“哪,相好是咋回事?”
“说是相好,其实是大家伙儿对老李戏噱地说法。女娃被接走了,那疯女人在精神稍好一点的时候就常常哭,老李就时常去看看她,给她送点吃的。村上的人熟了,见老李爱说笑话,就打趣说他是去看相好。”
老李的“相好”是个精神病人,一个地地道道的疯子,这一点我做梦也不会想到。听汪有才这么一说,我觉着浑身不自在,就好像做了贼被人当面不指名不道姓地辱骂一样。于是,这顿饭也就吃得滋味全无。
汪有才可能已经看出了我的内心,不过他人极聪明,没有直接揭我的疮疤,而是转了个弯子说:“你专门来打听老李的相好,是不是听到了什么话说?认为老李也象社会上流传的瞎话一样村村都有丈母娘?”
“不是不是!”我急忙否定。“老李是我小学时的同学,我们俩的关系一直不错,可这些年不在一起,关系也疏远了,对他的情况知道得太少了。这次是个难逢的机会,我就想多了解一下我这个老同学。”
说了这么多,实际只有一句话,那就是为自己开脱。我暗自庆幸没有在和汪有才谈话之前把这事说出去,要不我这人确实就丢大了。汪有才虽然没有再说什么,但从他似笑非笑的眼神里,我知道他并没有相信我的扯淡。
到了这一步,再坐下去已经没有意义。我正思谋如何全身而退,有才的儿子从学校回来了。一进门就对我说:“刘叔,我谢叔叔到处找你哩。”
这可是遇到了救星!可我还是不紧不慢地问:“他找我有啥事?”
“这我就不知道了。”
【未完待续】
鲁 旭 | 陕西凤翔县人,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戏剧家协会会员,陕西省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陕西省民俗学会理事,凤翔县作协主席。1978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风流街》、《下乡纪事》等小说作品,《二娃审案》等戏剧作品,《凤翔民俗》(上下卷)等。
【悦读推荐】
怀念湿地
责任编辑:辛 克
文字编辑:李 强
◆ ◆ ◆ ◆ ◆
【关注我们】
【凤翔作家&时光捡漏】新媒体联盟
时光捡漏 ∣您的生活笔记
公众号ID:xinke19820728
人生 · 生活 · 活着
了解凤翔讯息,敬请扫码关注《凤翔视窗》头条号和企鹅号
《凤翔视窗》头条号 《凤翔视窗》企鹅号
相关推荐
友情链接
Copyright © 2023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北京物流信息联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