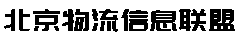「喪葬禮制」專輯
2016年12月16日至18日廈門大學歷史系召開「中國古代喪葬禮制青年學者研討會」,共有21位青年學者與會,分別進行專業報告,熱烈討論。會後張聞捷與游逸飛商議撰寫會議報導,進而以「古代中國研究青年學者研習會(二十二)」的名義,邀集部分與會學者惠賜相關稿件,組成「喪葬禮制」專輯,在「先秦秦漢史」公眾號上推送,拋磚引玉,以饗學界。這也是古代中國研究青年學者研習會第一次嘗試舉辦的網路活動。歡迎大家支持研習會,惠賜相關文章,充實「喪葬禮制」專輯。
![]()
![]()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莫阳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在本文中,我尝试将![]() 墓视为一件作品来解读。当谈到一件有形的作品时,浮现在人们脑海中的通常是雕塑、绘画、书法、工艺品以及建筑等等。但却很少有人会把城市或者陵墓当成作品来解读。虽然有一些学者也将墓葬的某些层面当成艺术分析的材料,然而将陵墓整体视为独立作品的情况仍然是相当罕见的。
墓视为一件作品来解读。当谈到一件有形的作品时,浮现在人们脑海中的通常是雕塑、绘画、书法、工艺品以及建筑等等。但却很少有人会把城市或者陵墓当成作品来解读。虽然有一些学者也将墓葬的某些层面当成艺术分析的材料,然而将陵墓整体视为独立作品的情况仍然是相当罕见的。
那么,是否可以将墓葬视为一件作品来阅读呢?我想答案是肯定的。如果我们考察墓葬的营建过程,以及建成之后的使用,不难发现多种不同的角色参与其中。不同参与者之间的互动,直到墓葬的最后完成,就是一件作品构思、设计、推敲、定稿,到付诸实施的过程。而墓葬建成之后的使用,则是相关角色面对作品、体验作品输出效果的过程。另外墓葬除了深埋地底的墓室外,还包含一系列地表之上的陵园景观,因而在建造完成后也面对来自他人和后来者的审视,这显然又涉及作品被认识和接受的层面,甚至往往会造成多重观念的叠加。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不同墓葬所能动用的资源和参与角色的范围必然有所差异。换而言之,就是不同墓葬消耗的成本有高低之分,因此呈现的效果也就有所不同。当然,成本的投入绝不仅仅只是由拥有资源的多寡而决定的,制度、习俗、观念、文化等等因素也从不同的层面影响作品的最终形态。
帝王的陵墓虽然用于埋葬死者,但毫无疑问也是国家最高礼仪的物质载体之一。它们既用于彰显死者的荣耀,亦供生者祭祀与观瞻。营建君主陵墓必然动用最大量的人力与物力,以保证呈现最高水平的工艺。参与者包括君主(本人或嗣君)、重臣、匠师等。如果我们将君主视为赞助人的话,他们个人的好恶实际上左右了陵墓的设计与建造。大臣们提供了礼仪的诠释与陵墓的规划,匠师则承担具体的营造;前者近似于建筑设计师的角色,后者相当于工程师的角色。总体的规划理念来自于设计者,具体细节则可能为匠师们留出了发挥才能和想象的空间。不同角色的互动与配合才使得陵墓营造得以最终完成。由此看来,有理由将君王陵墓视为一件超级复杂的作品。
陵墓营造中哪一部分更多是君主的意志,哪一部分是大臣的谋画,哪一部分是匠师的创造,很难在文献中获得足够详细的信息。当然,即便文献有足够细致的记载,我们也很难断言某一部分全然出于某甲、某乙的意见,而没有受到其他角色的启发与影响。即便如此,当我们把陵墓当成作品阅读时,抽绎和剥离不同角色意志对作品呈现的影响仍将是一种有趣的尝试。
更具体到墓的语境中,兆域图铜版的出土,为我们探讨整个陵园的设计规划和营建过程提供了一条明确的路径。
一、中山王的理想——兆域图
在遭盗墓者洗劫的中山王墓椁室中,发现了一块铜版。这块铜版曾为大火焚烧,又被坍塌的卵石压砸,出土时已严重变形碎裂。与墓出土的其他精美器物相比,它看起来毫不起眼。
在经过精心修复之后,人们发现铜版的一面显露出规整的图形和文字。(图1)其上所绘、所写构成一份详细的平面图,与墓地表陵园的布局直接相关。铜版上的平面图以金、银错嵌而成,铭文称:“为逃(兆)乏(窆)阔狭小大之别”。结合图文内容和墓的实际营建情况,学者普遍认为铜版的内容就是墓陵园的规划设计图。按《周礼•春官•冢人》称:“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为之图”。考古报告因此将该铜版命名为“中山王兆域图铜版”。从目前的材料来看,中山王墓“兆域图”铜版是已知最早的平面规划设计图实物。
![]()
1、为兆窆阔狭
兆域图大致分为三个层层嵌套的区域。(图2)最外一层为错银镶嵌的矩形方框,上边正中开一缺口,缺口两侧线条末端明显加粗,缺口处有一“闵”(门)[1]字。此外,在矩形方框四边还规律分布着七处注文,内容均为“中宫垣”[2]三字,叠压在四边线条之上。最外层的矩形错银方框,应表示的是陵园的中宫垣,且中宫垣在上方正中开一门。
中宫垣内的第二层区域,同样用错银的矩形方框表现。矩形方框的四边与中宫垣平行,在矩形上边框与中宫垣对应的位置也有一标有“闵”(门)字的缺口,且矩形四边的七处注文也与中宫垣注文位置一一对应,为“內宫垣”三字,可知第二层区域表示的为內宫垣墙。与中宫垣不同的是,在表示内宫垣的据矩形下边框,还开有四个缺口,每个缺口下接大小相同的正方形方框,方框内注文分别为“诏宗宫方百尺”、[3]“正奎宫方百尺”、[4]“执帛宫方百尺”、[5]“大宫方百尺”。[6]中宫垣内为内宫垣,內宫垣上方正对中宫垣门的位置开一门,下方开四门,分别连接陵园内的四处宫室。
第三层错银的线条较“中宫垣”、“內宫垣”更细,大致勾勒出一个呈“凸”字形的闭合空间。在凸字形边线上有八处注文,内容为“丘”[7]二字。凸字形闭合空间之内,是错金镶嵌的五个正方形方框,中间三个较大,外侧两个较小。五个正方形方框横向排列,以中间方框为中心对称分布。位于正中的方框内有“王堂方二百尺”字样,[8]王堂左侧方框内为“哀后堂方二百尺”,王堂右侧方框内为“王后堂方二百尺,其葬视哀后”。哀后堂左侧,稍小的正方形内为“夫人堂方百五十尺,萆(椑)桓(棺)、中桓(棺)视哀后,其题凑长三尺”;王后堂右侧,稍小的正方形内为“□□堂□□□尺,萆(椑)桓(棺)、中桓(棺)视哀后,其题凑长三尺”。
此外在凸字形闭合空间之内、王堂上方的位置,有三行铭文:“王命赒:为逃(兆)乏(窆)阔狭小大之□,有事者宣图之。律退致窆者,死无若(赦)。不行王命者,殃连子孙。其一从,其一藏府”。
![]()
这段铭文共39字,为我们解读兆域图铜版提供了最关键的信息。首先,通过“王命赒”三字,可获知关于设计者的关键信息,即这份陵园规划设计图是中山王委托相邦司马赒所制。“为兆窆阔狭小大之别,有事者宣图之”意为规划陵墓各区域大小的标准已经确定,可按此(标准)实施,点明铜版的功用;“律退致窆者,死无若(赦)。不行王命者,殃连子孙。”按照律令离开的人若擅进入陵园,死罪无赦。不遵从王命令的人,其罪要连坐子孙,这句则申明保护陵园的法令;最后一句“其一从,其一藏府”,涉及对铜版的保存,可知相同的铜版制作有两件,一件随葬墓,一件藏于府库。
2、作为作品的兆域图
据《周礼》可知,古代户籍和土地之图,大多保存于木板之上。版,从半木;板从木,二者互通。书籍插图称图版,地图称“版图”,其称谓均源于此。[9]而兆域图被铸造与铜版之上,从所选媒材来看,便显得别有意义。
兆域图铜版面积约5000平方厘米,厚度却仅0.8厘米,保证其铸造得平整已非易事。因其不容易成形,所需技术难度高,尤其铸造对象是比例精准的地图。若通过一次成型的铸造,对胀缩率的把控要比直接绘制图形复杂数倍。铜和金银等贵金属的使用,也使其制作成本大大提高。因此可以说,兆域图铜版是对作为规划设计图的“兆域图”本身的一种奢华呈现——以青铜铸造、金银错嵌的方式制作。因为金石不朽,铜版显然比之木板、布帛便于长久的保存。
铜版的长边恰好为短边的两倍(长95.6、宽48厘米),这种情况也提示我们,也许是出于对兆域图铜版外观规整的需求,兆域图中两重宫垣的比例被压缩了。因为丘内严格的比例尺表明,在制图的技术层面,对比例的控制并非难以达到的,出现这样的“失误”应并非巧合,更可能出于对图和载体美观的双重考虑。
研究者往往因为铜版上所绘制“兆域图”的价值,而忽视了兆域图铜版本身所使用的表现手法。将兆域图铜版视为作品(而不仅是工程图)进行细读,不难发现除了其“图”的功能外,版式设计也极精美。图注文字的方向、图形线条的颜色和粗细,无不遵循一定的设计原则,而呈现出超越地图意义的美观。
兆域图铜版的主体为青铜,在铜版的正面使用了金银两种材质的贵金属。金和银的使用主次有别,兆域图运用了不同材质的颜色对不同部分加以区别或强调:线条的粗或细;填充线条使用金或银,各表明不同的功能或重要程度。这种细微差异是仅通过线图无法领会的巧妙之处。
兆域图在绘制时除了自身具备的方向外,其图注文字的排布也遵从轴对称的原则,除主要宫室(包括两道垣门、五堂和四宫)图注文字为正向外,其他文字皆对称分布,文字方向从四面指向图的中心,即王堂所在的位置,这与陵园整体规划原则是相一致的。尽管这种版式设计的核心是以视觉手段体现等级秩序,却也呈现出一种由极端秩序感带来的美观。(图3)
![]()
3、修正的方案
兆域图铜版作为规划设计的最终方案被放置入王的椁室之中,对于死者、他的继承人,以及大臣们而言,显然有特殊的意义。纵然放入墓中的物品都可以概称为随葬品,但兆域图的置入其意义绝不仅仅只是随葬而已。
以往,人们不论从哪一角度审读兆域图,都只注意到它最终呈现的面貌。然而,我更愿意从另一个视角来观看。兆域图的细节清楚地告诉我们,它不仅仅只是最终的定案,而且还有多方讨论并敲定的过程。在我看来,最终定案固然重要,方案的讨论和修定过程可能更有意思。
通过对兆域图铜版实物的观察,我发现了一些报告线图并未呈现的痕迹,并且也是以往学者们没有注意到的。(图4)
![]()
根据残留的痕迹判断,兆域图铜版在最初铸造时,丘的形状与两重垣墙一样为长方形。但在铸造完成后,错嵌金银前,将代表丘的长方形边框的左上和右上两角边线空余了出来,又在其下折角的位置重开两细沟,填入银线,将丘的形状由长方形变为了“凸”字形。(图5)因此在铜版上,有两段方折的浅沟未被填以金银线。
![]()
在进一步讨论之前,我们有必要质问:这一痕迹的出现是由于制作工艺的需要造成的,还是有意为之呢?我认为答案是后者,也就是说,这是一次事后有意的修改造成的。从中山王墓出土的其他复杂而精美的错金银铜器来看,中山国的错金银工艺无疑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这一点学界是普遍认同的。处理兆域图上的这些直线条,对于当时高水平的工艺而言,显然并非难事。而且,如果细心观察的话,不难发现图4所示丘“凸”字形框线的修正部分与原先长方形框线存在打破关系。换而言之,这是二次修改所造成的。
从工程施工角度来看,丘形状如此调整确实节省了相当的土方量。[10]然而,问题在于,这样的修正仅仅是出于节省土量的考虑?还是另有原由?我们不妨先来看看这样的修改在视觉感受上会有何差异。
根据兆域图的规划,墓的陵园大致可分为四个部分:两重宫垣、承担祭祀功能的四座宫室、主体建筑下的高台(即丘)和作为陵园主体的属于中山王及其配偶的五座堂。如果按照最初的规划方案,中部五堂建在长方形的台基上。尽管五堂的体量大小有别,但这样的设计即便有主次之别,还是容易给人以等量齐观之感。进行修正之后,台基平面呈“凸”字形,暗示了居中部分的主体地位,而这里恰恰正是王堂和两后堂所在。
既然兆域图是中山王命令相邦司马赒所做的规划设计,那么司马赒就是方案的提供者,而则是方案的审定者。我们可以设想,中山王陵园布局的设计一定是经过多次往复讨论和修改的。并且只有商讨完成的“兆域图”才会被铸刻在铜版之上。而兆域图铜版上的修正痕迹说明,司马赒提供的设计方案即使在敲定并付铸版之后,还是没能达到理想中的效果。因此才有铸版之后的二次修正。修正之后的方案,才最终满足了对其王陵的想象。而这一过程无疑表明对陵园规划的高度重视。
二、兆域图的图绘与尺度
1、兆域图中的关键因素
针对兆域图的解读前人已有较为成熟的成果,其中最重要的是建筑史领域中傅熹年和杨鸿勋进行的研究和复原工作。[11]这些工作基本解决了兆域图阅读中的技术问题,将之转译为符合今天建筑规范的规划图。但是建筑复原细节等方面,学界仍然存在不同意见。
(1)尺度[12]与复原
兆域图作为墓陵园的设计规划图,其上除去图形、与图形对应的名称外,还包含部分图形的实际尺寸和相对距离的数据。这对复原墓陵园是极为难得的材料。
方位
古称“准望”,是地图的基本要素之一。兆域图上没有明确标明方向,但通过读图也能大致推断。尽管兆域图中注文朝向不一,但通过王堂等主体文字的方向,仍可判断兆域图绘制的方向,即两重宫垣门所在的方位为上。墓为南北向中字型大墓,主墓道南向。另外,在墓陵台最南一级底边外的中部,发现有瓦片堆积,说明当时可能在这里建有门阙。由此可知兆域图正向为南向。那么兆域图的方位即为上南下北,左东右西。东库出土的墨书木条DK:84一面墨书“宝重椁石”,两侧各书一“左”字,(图6)若如兆域图以南为正向,东库确为椁室之左,是为印证。另外时代稍晚的马王堆三号墓出土《驻军图》标示方向亦为上南下北。
![]()
单位
兆域图中的图注标明了图形间的距离和建筑的尺寸,在全部38处距离的标注中,以“尺”为单位计量的24处,以“步”为单位计量的14处。有学者认为这是由陵园规划上的要求不同决定的,丘以内的主体建筑要求尺寸精准,用“尺”标注;而其他部分在精度上就粗略,使用步。[13]
比例尺
裴秀称地图的比例尺为“分率”,《隋书·宇文恺传》载宇文恺在《明堂议表》中提及其所绘之《明堂图》“裴秀《舆地》以二寸为千里,臣之此图,用一分为尺”,可知至少在隋代即有比例尺的存在。而根据兆域图的实际尺寸和图注尺寸,也可以得之兆域图制图遵循一定比例。
尺 兆域图标注尺寸与实际尺寸基本合乎比例。如铭文标注方二百尺的王堂、王后堂和哀后堂,实测为8.6-8.8厘米;铭文标注为一百五十尺的两座夫人堂,实测为6.5-6.65厘米;而王堂与两王后堂间距标注为一百尺,实测为4.4厘米。铭文标注尺寸与实测尺寸比例精准,且可换算出兆域图的大致比例尺为一百尺等于4.4厘米,即一尺等于0.044厘米。已知战国时期尺的长度约合22-23厘米,则可知兆域图的比例尺约为1:500。[14]
步 兆域图中,丘至內宫垣、內宫垣至外宫垣的距离以步为单位。与《考工记》“野度以步”的记载相合,这些以步为单位测量的部分均为露天平地。傅熹年在《战国中山王墓出土的<兆域图>及其陵园规制的研究》一文中,首次计算出兆域图中两种计量单位的比例关系,即一步等于五尺[15]。
尺度与图像的矛盾
兆域图中以尺为单位的图形与间距都是严格符合比例的;而以步为单位的间距则不然。这样看来兆域图中,尺的标注精确,而以步标明的部分则仅为示意。也就是说,在兆域图中,按比例尺准确描绘的部分是宫室、丘及丘上的五堂;而代表內宫垣和外宫垣两条边线的比例与标注尺寸不符。
一方面在工程图中,单位的使用有较严格的规定,两种尺度单位的不同可能与具体施工的相应环节有关。另一方面,则可能是局限于兆域图铜版的大小,为了凸显主体部分的重要性,对两重宫垣分别进行了压缩,以减小整张图中空白的面积。不管是出于何种原因,我们仍需要对兆域图铜版进行等比例的复原和翻译。(图7)[16]
![]()
(2)尊卑:尺度反映的观念
除了对准确比例的复原外,还应意识到兆域图各部分尺寸实际上反映了一定观念。
兆域图所绘丘之上的堂类建筑共五个,总量为奇数,因此有明确的中心。与此近似的还有辉县固围村战国墓群。(图8)三座墓葬横向并列,其上有尺寸不一的封土,根据地表的遗迹情况判断,封土上原有建筑。固围村墓葬与兆域图平面布局相近,同样是奇数个的墓上建筑,这样在陵园的平面上自然呈现为以居于中间个体为主体的布局方式。另外在封堆体量上的区别也贯彻这一设计,居中的M1封土尺寸大于分立其两侧的M2和M3。兆域图所绘属于和其配偶们的五堂中,位于“凸”字形丘突出部分的三堂,在所处位置和大小上,都较夫人堂为重,显示出墓主的尊贵地位。三堂中,显然又以居中的王堂为轴线中心。王堂与对称分布于两侧的哀后堂、王后堂在体量上并无差距,都是方二百尺。实测墓(M1)西侧的二号墓(M2)回廊面积与一号墓相同,也可与兆域图规划相互印证,但二号墓回廊的地面低于一号墓,相当于一号墓散水标高,垂直高差达到1.3米,这是兆域图中并未反映,也难以反映的。
![]()
整体来看兆域图对墓陵园进行的规划,在平面上呈现出规整的轴对称布局,越靠近中心对称轴的部分,越显示出重要性。轴线穿过王堂正中,王堂两侧对称排列的是与王堂尺寸相当的王后堂和哀后堂[17],作为王的妻子,王后有资格享有与其夫同等的墓葬规格,但在等级观念严苛的时代,男尊女卑的思想仍占据主导,因此可以看到在实际墓葬的建造中,哀后堂在立面上低于王堂,从而凸显出王堂的绝对权威,这也是符合兆域图整体设计理念的。在哀后堂东侧和王后堂的西侧,两夫人堂对称分布,其尺寸小于中三堂,且位置较中三堂靠后(北侧)。
总的来说域图对陵园进行的规划有两个显著特点:几何性布局,强调对称性。而这两者的作用都是凸显位于核心位置的王堂,核心是对等级秩序的视觉呈现。
2、“图绘天下”
《周礼·春官·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为之图”,郑玄注:“图,谓其地形及丘垄所处,而藏之先王造茔者”。兆域图的性质显然是战国时期地图之属。
文献中关于地图的记载出现极早,有学者认为在《诗经》、《尚书》等文献中,已有对地图的记述。[18]到春秋战国时期,记录山川地貌的地图在文献中频繁出现,显然承担着极重要的功能。《周礼》有云:
大司徒之职,掌建邦之土地之图与其人民之数,以佐王安扰邦国。以天下土地之图,周知九州之地域广轮之数,辨其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之名物,而辨其邦国都鄙之数,制其畿疆而沟封之,设其社稷之壝而树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与其野。[19]
大司徒作为地官之首,除了掌管户籍外还保管“土地之图”。地图是国土的象征,掌握地图的行为预示着占有土地。尽管《周礼》作为文献有其理想化的一面,但对照《史记·萧相国世家》记载,刘邦初入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刘邦在其后与楚的争霸中“具知天下阨塞,户口多少”都是得益于萧何在咸阳所得的秦图书。可见由官员掌管国家图籍的方式是确实存在的,这些地图内描绘的信息精准反映国情,因此地图的保管和流失更是关乎重大。
《战国策·秦策》有“据九鼎,按图籍,挟天子以令天下”的言论;《燕策》和《史记》对荆轲刺秦之事的记述中,荆轲得以面见秦王的理由之一即假意进献燕督亢地图,对此“秦王闻之,大喜,乃朝服,设九宾,见燕使者咸阳宫”[20],秦王如此排场,并非因为得到区区一张地图,而是即将占有督亢地图所代表的土地,不费吹灰之力而得到燕国要地,显然是值得大喜的事情。
谭其骧认为先秦时期地图绘制水平高与法家的流行有关,因为法家在军事上要求取得统一战争的胜利,,所以必然重视地图。因此在与法家有关的先秦论著中,不乏对地图功能的强调。这与上章所言中山三晋在战国中期的治国方略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管子·地图篇》强调地图在中的重要性:
凡主兵者,必先审知地图,轘辕之险,滥车之水,名山、通谷、经川、陵陆、丘阜之所在,苴草、林木、蒲苇之所茂,道里之远近,城郭之大小,名邑、废邑,困殖之地,必尽知之。地形之出入相错者,尽藏之。然後可以行军袭邑,举错知先后,不失地利,此地图之常也。[21]
把控地图有掌管一个区域之意,这大约源于征伐战争频发的春秋战国时期。地形、地势是战争中可利用的致胜因素,因此地图对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与兵力和武备这类硬实力相比,将山川河流的面貌准确呈现,也是各国倾力而为的军事情报。正是在这样需求的推动下,战国时期地图的绘制水准也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出于对准确性的要求,逐步发展出一套科学的制图准则。作为具有高度实用性的“图”,图形的准确和信息的详尽是地图的重要特点。
但由于图的制作和复制较书籍传抄更为困难,因此尽管“图书”并称,但“图”的流传远少于典籍的传抄。幸而近年来的考古发现部分的弥补了这种遗憾,如天水放马滩秦墓出土地图(图9)和时代稍晚的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地图等,[22]都是极珍贵的古地图实例。我们也因此知道战国到汉初时期确实存在如文献描述那样精准的地图,而并非像裴秀所言汉代地图“各不设分率,又不考正准望,亦不备载名山大川,虽有粗形,皆不精审,不可依据”[23]的情况。
![]()
兆域图基本具备“制图六体”,[24]遵从特定比例精确制图,亦有自成体系的详细图注,反映了战国时高超的地图绘制技术。但兆域图与放马滩秦墓或马王堆三号墓所出地图不同,并非是针对山川、河流或村镇等客观事物的描绘,、军事需求相去甚远,而是对尚未建起的陵园景观的规划与设计。
早期文献和出土地图实物,反映了战国时期人们对景观的观察和提炼已经逐步脱离了感性阶段,走向理性认识。人们开始有能力掌控对大尺度景观的图形表现,可以将三维景观缩微到二维的平面之上。兆域图的例子进一步证明,在战国时期已经有能力将对三维空间的设想呈现于二维平面,再经由人力实践将其从方寸平面“搬”到现实世界中,创造新的人造景观。
抽象思维能力的提升,使人们对山川地理的审视转向一个新的阶段。这可被视为发生在视觉和思维层面的双重转向。与今天的地图一样,兆域图等古地图所呈现的观察视角是垂直俯视,在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期,这一视角显然不是自然之眼可捕获的,而是经过理性思维进行抽象总结后的结果,即理性思维的视觉化呈现。更难能可贵的是,这种理性思维不仅能被用于总结客观存在的山川地貌,也可以用于表达和呈现对人工创造的细致规划。
(本文節錄自《中山王的理想——兆域图铜版研究》,《美术研究》2016年第1期。)
为适合微信发布,注释省略,引用请参考原文。
“先秦秦汉史”公众号正在推送“喪葬禮制专题”,本专辑由古代中國研究青年學者研習會(張聞捷、游逸飛)策划统筹,期待大家有相关文章都可发来(xqqhsyj@126.com)。让学术有情怀地飞扬起来!
图文编辑:姚磊
![]()
我们致力于学术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