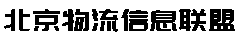苏轼军事才能的确是被低估了
![]()
北宋之世,始终面临着北方辽国与西边西夏的军事威胁。崛起于沙漠之间的契丹民族所建立的辽国,时不时以举兵威胁北宋朝廷,要求增加岁币,宋廷则不愿再构边衅,往往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背上了沉重的财政包袱。而西夏的侵扰,军事上的失败,,而且使财政出现了严重困难,从根本上侵蚀着北宋的立国根基,同时,还极大地打击了北宋士人的华夏正统意识,使其夷狄观产生了巨大变化。这一切都使苏轼对军事形势的变化、军事策略的谋划、军事制度的改革等极为重视,并专门著篇论述之。
苏轼在对御试策中希望仁宗与诸大臣能够“留意于大者”,所以他对军事问题的论述,也并非单纯的就事论事。他首先具有一种宏阔的全局观,尤其注重军事成败与社会、经济稳定的关系。他固然认为辽国与西夏对北宋有一些威胁,但更重要的是内政的稳定 “夷狄抗衡,本不能为中国之大患。”“西戎、北狄,不足以为中国之大忧,” 他强调应当重视“内之民”的反抗,可怕的是“其动也,有以召内之祸,”他指出内忧外患之间的紧密关系:“内之民实执其存亡之权,而不能独起,其发也必将待外之变”。〈策略三〉北宋王朝的存亡,实际上掌握在辗转在战争中的贫苦百姓手中。 但是,欲安内必先攘外,“二虏之使未决,则中国未知息肩之所……二虏之大忧未去,则天下之治终不可为也”〈策略二〉要使北宋的统治长久地统治下去,必须有一个安定的周遍环境,必须减轻岁币给北宋王朝带来的沉重负担。所以他宣称,当时北宋王朝的岁币政策是“弃有限之财,而塞无厌之心” (《休兵久矣而国益悃》)并指出:“中国以禽兽视二虏,故每岁啖以厚利,使就羁绁。……然夷狄贪惏,渐不可启,日富日骄,久亦难制。故自宝元以来,赋敛日繁,虽休兵十有余年,而民适以困者,潜削而不知也” 。“潜削而不知”一语,准确地说明了北宋王朝在表面上安定的环境下所面临的危殆之境。
但是,苏轼在军事上的独到之见并非对国家大势之判断,而是在具体军事策略上的布局与谋划。他在《策断》诸篇中详细地论述了自己对辽国、西夏、北宋三国形势以及斗争的策略。苏轼的这些观点既有年少轻狂之论,也有罔顾历史情势之谈,但也不乏辨析精微的真知灼见,即便是在不切实际的观点之中,也潜含着某些合理因素,实在不可一概而论。那么苏轼之观点具体在何处有阙失,又在何处显示出其透辟的眼光呢?我们不妨将之细加厘清。
![]()
苏轼首先主张要准备与辽国、西夏进行斗争,必须设立具体的处置部门:他认为“今之所以待二虏者,失在于过重。”(策略二)何以言过重?苏轼指出:“今者二虏不折一矢,不遗一簇,走一介之使,弛数乘之传……于是朝廷汹然,大臣会议,既而未去数月,边遽且夫告至矣。”甚至“二虏之未动也,而吾皇吾相终日皇皇焉应接之不暇”。因此他主张仿周代行人、西汉典属国之制,“特建一官,重任而厚责之,使宰相于两制中,举其可用者,而勿夺其权;使大司农以每岁所以馈于二虏者,限其常数,而预为之备;其余者,朝廷不与知也。”在苏轼的设想中,这一官职有着充分的自主权,“凡吾所以遣使于虏,与吾所以馆其使者,皆得以自择。而其非常之辞,无厌之求,难塞之请,亦得以自答,使其议不及于朝廷。而其闲暇,则收罗天下之俊才,治其战攻守御之策,兼听博采,以周知敌国之虚实,凡事之关于境外者,皆以付之。”举凡外交、军事、用人之权,皆握其手。苏轼并且以为使其“日夜思所以待二虏,宜无不济者”。细察苏轼之本意,其实在于以内政为重:“中书常有蛮夷之忧,宜其内治有不办者”,而“天下之大计”也因二虏之掣肘未能详加讲求。但是苏轼此设想却完全违背了北宋王朝之家法。北宋立国之初,太祖太宗鉴于五代多乱臣的教训,便于设立官制之时细加谋划,,并使臣下上下牵制,以消除臣下对君主的潜在威胁。 虽然导致“官制丛脞”(顾炎武语)乃至行政不畅的局面,却有利于皇权的稳固。因此,宋廷决不可能放手将外交军事用人大权交付一人,以养成尾大不掉之势。而纵然真如苏轼所议设立其职,在北宋谏官横行的形势下,恐怕不久也会因谗言而罢废。所以苏轼此论其实更近少年空谈屠龙之计而已。真正有价值的还是其对实际战争形势的估计。
在对辽国的斗争策略上,苏轼提出结交西域诸国以对辽国形成夹击之势,而在联盟结成之前,暂时对辽国采取策略性的防守态势。他明确指出:“古之制北狄者,未始不通西域,今之所以不通者,是夏人为之障也”,故在三国博弈之中,主张首先攻取西夏,以扫清与西域交通的现实障碍,为抵御辽国做更强大的防卫。此论突出反映了宋代士大夫对西夏的蔑视与对辽国的畏惧之心。北宋朝廷与士大夫向来以北边为重,而视西鄙之地为次要的威胁。在西夏初反宋之时,宋太宗和大臣就认为“党项号为小蕃,非是劲敌,试如鸡肋。”〔29〕及至元昊建国并在陕西之战中三败宋军,宋仍未把西夏作为真正的对手。欧阳修说:“天下之患不在西戎而在北处。”〔《历代名臣奏议》卷326〕张耒说:“西小而轻,故为变易,北大而重,故变为迟。小者疥癣,大者yōng疽也。”〔《柯山集》卷40,《送李端叔赴定州序》〕甚至曾经主持西夏防御战争的范仲淹,竟然也说出“国家御戎之计在北为大”这样的话来〔《历代名臣奏议》卷324〕,可知苏轼所说:“西边患小,北边之患大,此天下所明知也。”〔《策断中》〕实在并非空穴来风,而他自己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当时风气的影响。 当然,宋人对契丹、西夏重轻之论,不过是比较而言,并非完全忽视西夏这样的“戎汉余妖,边关小种”,(《削赵元昊官爵除去属籍诏》)西夏之连年侵扰,已经对北宋边境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使北宋的稳定受到了严重的威胁,给宋造成的国防压力远远甚于契丹,在战略上同样应该予以高度重视。更何况没有人会不知道“柿子捡软的捏”的道理,苏轼绝对不会去干横挑强邻的蠢事,所以他一再强调辽国的威胁,也不过是主张小心翼翼维持着与契丹的对峙局面,而对小小“西贼”则不遗余力地力主出战。单就此论本身而言,纵横捭阖于各国之间以谋取自身利益,:宋隔西夏与西州回鹘、黄头回纥遥遥相望,更远处还有黑汗(喀喇汗)回鹘,倘若交好回鹘,自然会对辽国的布防造成一定压力。但这并非便意味着苏轼的想法便无懈可击,实际上,苏轼策略的实现存在着两个前提:一是宋廷的实力,二是能否战胜西夏。。在宋廷屡战屡败,甚至基本上没有翻盘希望的情况下,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贸然上了宋廷这条虚弱不堪的破船。但事情的转机就蕴藏在与西夏的战争之中。倘若宋廷能够顺利击败西夏的侵扰,甚至掩占其地以与回鹘诸国边界相连,不但使得此策有了实现的必要条件,而且还能够证明宋廷自身的军事力量。那么苏轼是如何谋划对西夏战争的呢?
当时在宋廷内部,大多围绕着两个问题争论不休:一是与西夏是战是和?二是在战争总体的指导方针的确定上,是以守为主还是攻为主?就当时情势而言,西夏初叛之时,兵强马壮,风头正劲,而且是有备而来。反观宋朝,除了数十万已经习于恬安,不谙战阵的军队外,一无所有,当此之时,不宜轻动。最为妥当的策略应当是先阳许其求,而暗中厉兵秣马,修缮军备,准备齐全之后再行讨伐。而战端一开,则必须坚持到底,不能轻言媾和,否则必然会导致与辽宋战争同样的结局。宋廷在这一问题上,未始没有目光犀利之人。比如吴育、范仲淹等人就多有持重之意。但许多文官论兵,众议纷纭,只知维护宋廷体面,却不解时势,所以其政策仍然是始之以自大,自居上国,贸然出兵;终之以自卑,唯求防御,不思进取,始终在或战或和之间犹豫不决,摇摆不定,致使“权常在敌”,不但在战争中屡战屡败,而且在外交上也频频丧失先机。 苏轼指出:当时“贼非能常战也,特持其常战之形,以乘吾欲和之势,屡用而屡得志,是以中国之大,而权不在焉。欲天下之安,则莫若使权在中国。欲权之在中国,则莫若先发而后罢。示之以不惮,形之以好战,而后天下之权,有所归矣!”何谓权?“千钧之牛,制于三尺之童,弭耳而下之,曾不如狙猿之奋掷于山林,此其故何也?权在人也。”“夫为国者,使人备己,则权在我,而使己备人,则权在人。”故苏轼以为宋朝应当“争先而处强”,采取主动出击的攻势。(〈策断一〉) 他主张坚决采取“战”的既定措施,使西夏无法借宋廷“欲和之势”进行要挟,索取岁币财货。而在攻守问题上,他更是兼顾攻守二道,对此谋划甚悉。
当时在战争攻守的问题上,宋廷内部纷纭难定。早在宝元二年(1039)六月,夏竦就上奏提出要“善治壁垒,修利器械,约束将佐,控扼险阻”,进行长期防御,并上教习强弩以为奇兵;羁縻属羌以为藩篱;募土人为兵以代东兵等十策。后期战守之争则主要是在韩范之间展开。主战的韩琦认为“臣以贼昊倾国入寇,不过四五万,老弱妇女,举族而行。……臣逐路重兵自守,势分力弱,故遇敌不支,若大军并出,鼓行而前,乘贼骄惰,破之必矣!”(《宋史纪事本末》卷三十)范仲淹主张严守:“为今之际,莫若且严边城使持久可守。实关内使无虚可乘,……二三年间,彼自困弱。”他认为出大兵进讨,战于沙漠之中,“无功而有患”。况且“今承平岁久,中原无宿将精兵,一旦兴深入之谋,系难制之敌,臣以为国之安危,未可知也。”(《长编》卷127)“泾原师出,败于好水川,天子由是益信公过人远甚。”(《范文正公仲淹墓志铭》)自此,宋朝内部才确立了以防御为主的战略方针。但是,值得指出的是,范仲淹虽主张采取守势,但并不等于盲目退缩,不思进取,只欲求和。在宋廷与西夏议和之际,他坚决反对对西夏的优厚待遇,主张对西夏予以坚决打击,免留后患。显然其意在于以长期顽强的防御,等待西夏国力疲敝之时,而后伺机重拳出击,彻底击溃敌人。
苏轼在这一问题上受范仲淹影响甚大。他主张在维持整体上的守势的局面下,采取分兵之策,局部发动攻势。分兵本来是宋军的大忌。当时抵抗辽国和西夏的边防前线东起海边的沧州,西至陇山外的秦州,绵延数千里多是无险可守的平原,必须处处屯列重兵,结果造成了“备多力分”的被动形势。欧阳修云:“庆历御边之备:东起麟府,西尽秦陇,地长二千余里,分为路者五,而分为州为军二十有四,而军州分为寨为堡者又几二百,皆须列兵而守之。故吾兵虽重,不得不分;所分既多,不得不寡;彼重虽寡,聚之为多;以彼之多,击吾之寡,不得不败也”(《长编》卷二0四) 即便是进攻,也常常会因为分兵而陷入绝境,夏竦上奏云:“若分兵深入,则军行三十里,自赉粮(米臭),不能支久,须载刍粟,难于援送。师行贼境,利于速战,倘进则贼避其锋,退则敌退其后,昼设奇伏,夜烧营栅,深可虞也。”夏竦之论并非危言耸听,其父夏承皓曾参加过太宗时追讨李继迁的战役,那次因为西夏避其锋芒,诱其深入,最终师老于外,不得不无功而返。但是苏轼既反对坐待敌至的消极防御战术,也异于妄图毕其功于一役的分兵深入之论,他明确指出:“臣之所谓分兵者,非分屯之谓也。使其十一而行,则一岁可以十出;十二而行,则一岁可以五出。十一而十出,十二而五出,则是一人而岁一出也。吾一岁而一出,彼一岁而是被兵焉,则众寡之不侔,劳逸之不敌,亦以明矣!”其意盖在于,利用宋军军员充足的特点,对敌人分兵骚扰。使其疲于防备,进而拖垮西夏经济。他指出:“夫用兵必出于敌人之所不能,我大而敌小,是故我能分而彼不能,此吴之所以肆楚,而隋之所以狃陈欤?”因此,他自信地宣称:“夫御戎之术,不可以逆知其详,而其大略,臣未见有过于此者也”。
除此之外,苏轼在抗击西夏的策略上,还主张“捐秦以委之”,部分实行屯田之制。“使秦人断然如战国之世,不待中国之援,而中国亦若未始有秦者”,他对此充满信心,并宣称如此则“有战国之全利,而无战国之患,则夏人举矣!”。表面看来,此论近乎奢谈,但究其实,他所谓的“捐秦以委之”,并非弃其土地人民,而谓独以秦地之力抗西夏之师,将秦地本身的人力与物力集结起来,与西夏对抗。苏轼早就指出过,西夏之所以难攻,实因“吾中国自困而不能举也”,“以不生不息之财,养不耕不战之兵,块然如巨人之病?,非不枵然大也,而手足不能以自举”。故以秦地付西夏,着眼之处仍然是尽可能地减轻西夏战争给全国财政带来的困难,以免使全国陷入战争的深渊,导致疲敝之境。 而以秦地一郡之力,何以抵抗西夏久经沙场的精兵良将?苏轼提出要以土兵作为御夏战争中的主力。土兵,既临边战区当地的乡兵,他们一般不脱离生产,“选自户籍,或土民应募,在所团结训练,以为防守之兵”,其战斗力相当强大,如弓箭手等“守边捍御,藉为军锋,素号骁勇。”充分利用土兵的意见夏竦早在1039年就曾经提出过。韩琦、范仲淹也都曾对此详加谋划。范仲淹指出土兵“月给差少,又素号精强”“比之东兵不乐田利,不习地势,复无怀恋者,功相远矣。”他在庆历元年十一月《攻守二议》中还指出守边多用远离家乡的禁兵,时间长久,必然会消弱军队战斗力:“或曰宜用守策,来则御之,去则未逐。臣观今之守边,多非土兵,不乐久戍,又无营田,必劳远馈。久戍则军情以殆,远馈则民力将竭,岁月绵远,恐生他患,此守御之未利也。”所以他提出要让陕西关内的土兵及其家人“并迁家于缘边住营,更免出军。父母妻子乐于完聚,战则相救,守则相安”。(《奏陕西河北攻守等策》)苏轼与范仲淹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并非完全利用现有的人力资源,而是主张对人力物力进行调配:“稍徙边缘之民不能战守者于空闲之地,而以其地益募民为屯田。屯田之兵稍益,则向之戍卒可以稍减,使数岁之后,边缘之民,尽为耕战之夫,然后数出兵以苦之,要以使之厌战而不能支,则折而归吾矣!” 所谓“稍徙边缘之民不能战守者于空闲之地,而以其地益募民为屯田”,其目的虽在于通过兵员的选拔,增强军队战斗力与凝聚力,但这种兵民合一的制度构想其实业已触及当时兵制的改革。
苏轼对兵制改革论述甚多。他指出当时兵制之患有二:其一在于养兵与戍守征行之制糜费财富。苏轼指出:“今天下之兵,不耕而聚于京畿三辅者,以数十万计,皆仰给于县官”。“天下之财,近自淮甸,而远至于吴蜀,凡舟车所至,人力所及,莫不尽取以归于京师。晏然无事,而赋敛之厚,至于不可复加,而三司之用,犹苦其不给。其弊皆起于不耕之兵聚于内,而食四方之贡赋”。苏轼还指出:“费莫大于养兵,养兵之费,莫大于征行。”“今出禁兵而戍郡县,远者或数千里,其月廪岁给之外,又日供其刍粮。三岁而一迁,往者纷纷,来者累累……农夫之力,安得不竭?馈运之卒,安得不疲?,而掌握郡县之厢军。其实际目的则在于以地方财政养兵,。苏轼指出:“夫土兵日以多,禁兵日以少,天子扈从捍城之外,无所复用。如此则内无屯聚仰给之费,而外无迁徙供亿之劳”。
其二则是兵民分离的募兵制度使军队战斗力下降而养兵之费增加。苏轼指出:“兵民既分……于是始有老弱之卒”。募兵制使得士兵“行不得为商,居不得为农,而仰食于官,至于衰老而无归”。“无用之卒,虽薄其资粮,而皆廪之终身。”因此当时宋军“养兵十万,则是五万人可去也;屯兵十年,则是五年为无益之费也”。苏轼痛斥“有兵而不可使战,是谓弃财;不可使战而驱之战,是谓弃民”。并感叹道:“臣观秦汉之后,天下何其惨败之多耶!其弊皆起于分民而为兵”。因此他主张“自今以往,民之愿为兵者,皆三十以下则收,限以十年而除其籍”。这样,“县官长无老弱之兵”而“民三十而为兵,十年而复归,其精力思虑,犹可以养生送死,为终身之计。”于国于民,皆无明显弊端。而且,百姓为兵一段时间之后,也可以使“天下知兵者众,而盗贼戎狄将有所忌”。
苏轼还极为重视对军事人才的选拔。在这方面他首先以治兵实效选拔将才。苏轼指出当时朝政“设武举,购方略,收勇悍之士,而开猖狂之言,不爱高爵重赏,以求强兵之术。”但是却导致“天下嚣然,莫不自以为知兵”,但“至于临事,终不可用”的局面。苏轼认为“天下之实才,不可求之于言语,又不可较之于武力,独见之于战耳。战不可得而试也,是故见之于治兵。”因此他主张。为选拔合适的将才,应当“武举、方略以来之,新兵以试之”。并从“气”“威”“能”三个方面来考察将官才能:“观其颜色和易,则足以见其气;约束坚明,则足以见其威;坐作进退,各得其所,则足以见其能。”苏轼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较之以可见之实,庶乎可得而用也”。
其次,苏轼还提倡收养心腹死士“倡勇敢”。他认为当时宋军在西夏面前的溃败就是因为“上作而下不应”,“天子无同忧患之臣,而将军无心腹之士”。而“致勇莫先乎倡,倡莫先乎私”。他认为“天下有急,而有一人焉奋而争先而致其死,则翻然者众矣!”“三军之士,瞩目于一夫之先登,则勃然者相继矣!”而“苟有以发之,及其翻然勃然之间而用其锋,是之谓倡”。故“天子必有所私之将,将军必有所私之士,视其勇者而阴厚之”。只有这样,才能“以难得之人,行难能之事”。
在梳理清楚苏轼的军事策略之后,我们有必要考察一下苏轼的夷狄观。苏轼夷狄之人相当蔑视。虽后来辽人对其文章节操倾心相慕,至有宋使者至则勤加问询。但苏轼却并未抱有宽容之胸怀,反于其文中屡屡加以贬斥。《王者不治夷狄论》以为戎狄“譬若禽兽然”,《休兵久矣而国益悃》言“中国以禽兽视二虏”,〈策断三〉则指戎狄有“犬羊豺(chai)狼之性”,即便是在单纯论述人性之说的《韩愈论》中,他也不忘将“待人之道”“待夷狄之道”“待禽兽之道”离而为三,视夷狄为非人。此虽当时士大夫之陈语,然亦可见苏轼成见之深。而其于此傲慢的表象之下,尚暗含多重之意蕴。对此其《王者不治夷狄论》一文中言之甚详。苏轼于此文中征引《春秋》之例,以为对戎狄若“求其大治,必至于大乱”,盖其“不可以化诲怀服”,“彼其不悍然执兵,已与我从事于边鄙,则已幸矣!”“不然,将深责其礼,彼将有所不堪,而发其愤怒,则其祸大矣!” 其间所透露之消息,首先便是对夷狄的忧惧之心。此段话中言夷狄“不可以化诲怀服”一语显然并非原始儒家“宾服四夷”,或“怀远人”之意,也与同时所作的苏辙之论判然有别。盖源出于《》的“宾服四夷”之论实表现了当时周王朝对自身文化的强烈自信心与自豪感,在德被天下的外衣下折射出的则是对自身文化生命力无限延伸的渴望。而苏辙之论则以为古之所以治夷狄之道:“有用武而征伐之者,……有修文而和亲之者,……有避拒而不纳之者”,“此三者皆所以与夷狄为治之大要也”。而“圣人之与戎狄也,吾欲来之则来之,虽有欲去者不可得而去也;吾欲去之则去之,虽有欲来者,亦不可得而来也。要以使吾中国不失于便,而置夷狄于不便之地,故其屈伸进退,莫不在我”,其间表现的则是在灵活性掩盖下的退缩,“王者”的“征伐”“和亲”与“避拒”实与自身强大与否密切相关,而多重选择的出现只能意味着“宾服四夷”的伟大理想的落空。、军事角力的主动性而巧妙地淡化了理想在现实中的黯然失落。但是在苏轼这里,甚至连那些多重的选择也悄然消隐:剩下的只不过对夷狄侵袭边地的深切忧虑,而这种忧虑本身便是北宋国家贫弱、文化精神衰退的心理映射。
正因如此,他在本文中强调:中国与夷狄制度不一,倘若强自以中国之礼乐文物教化夷狄之人,则必然激起其国之反感,乃至于引兵南下,与中国之人兵戈相见。在这里浮现的仍然是那种委琐心态。同时苏轼却也在无意间点明了辽宋之间游牧文化与农耕——礼乐文化的冲突。
苏轼对这种文化冲突的论断并非偶一为之。在《策断三》中,他再次指出:“各辅其性而安其生,则中国与胡,本不能相犯。惟其不然,是故皆有以相制,胡人之不可从中国之法,犹中国不可从胡人之无法也。”表述无疑更为明白透彻。他还在同一文中指出辽人因袭中国之制度之不可能:“今蛮夷而用中国之法,岂能尽如中国哉!苟不能尽如中国,而杂用其法,则是佩玉服?冕垂?而欲以骑射也。…… 以蛮夷之资,而贪中国之美,宜其可得而图之哉。”并引证春秋吴国,晋末五胡一传再传而灭之史实,以为夷狄“其心固安于无法也,而束缚于中国之法……是以虽建都邑,立宗庙,而其心岌岌然常若寄居于其间,而安能久乎?”而当时之辽人虽朝仪、官号、郡县、选举、衣服、饮食,皆“杂取中国之象”,但“其中未能革其犬羊豺(chai)狼之性,而外牵于华人之法,此其所以自投于陷阱网罗之中”。苏轼甚至以为倘若中国“其守以形,其攻以势,其战以气”,则“敌人莫不摄也”。
苏轼的这种判断,乍看之下似乎莫名其妙,而且惊人的武断。当时宋人都已意识到辽、夏之文化已皆如中原礼乐,富弼就曾说,“自契丹侵取燕、蓟以北,拓跋自得灵夏以西,其间所生英豪,皆为其用。得中国土地,役中国人力,称中国位号,仿中国官属,任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车服,行中国法令,是二敌所为,皆与中国等。而又劲兵骁将长于中国,中国所有,彼尽得之,彼之所长,中国不及。当以中国劲敌待之,庶几可御,岂可以上古之夷狄待二敌也。”〔卷150〕苏轼何以如此辱骂他们“未能革其犬羊豺(chai)狼之性”?而“外牵于华人之法”又当如何理解呢?
![]()
应当指出的是,苏轼对夷狄之人的辱骂只能证明他内心根深蒂固的优越意识,这点我们不可为贤者讳。。苏轼屡屡以“中国之法”、“胡人之无法”为言。中国之法,当然是指礼乐官制,那么“胡人之无法”是指什么呢?是貌似无法,实则灵活机动的部落制度。史书记载:契丹、西夏等夷狄之人士兵与首领之间“少长服习,盖如臂之使指”,(《西夏纪》卷八)“人人习骑射,乐战斗,耐饥渴,其亲冒矢石、蹈锋刃、死行阵,若谈笑然。”(《西夏纪》卷二八)《西夏书事》卷十一“元昊……每出兵,必率部长与猎,有获则下马环坐而食,割鲜估饮,各问所见,择取其长”。这很容易契合苏轼“通上下之情”的行政理想,故其称:“匈奴以无法胜”。但是随着国内经济文化的发展,辽国与西夏逐渐采取了中原官制,据《西夏书事》记载,(卷十一)西夏所设官员,不但中书、枢密、三司等重要机构,甚至还有开封府、磨勘司、文思院等机构。汉化程度愈深,则官制愈加繁复,原来那种上下之间亲密无间的状态也难以复现。而上下不交,上层官员与下层官吏难以达成通畅的信息交流机制,。故苏轼所谓的“外牵于华人之法”并非泛泛而谈,他具体针对的是华夏礼乐文明将使契丹王朝造成“上下悬隔”之弊。而上下悬隔无疑将会对辽国与西夏的战争机制产生深刻影响。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他才大胆宣称夷狄“自投于陷阱网罗之中”。
文/大荒九派
查看更多精彩内容请点击底部“阅读原文”继续关注
![]()
![]()
![]()
投稿方式微信号:QsgrQ138033389 邮箱:138033389@qq.com
![]()
以上内容来自网络或网友提供,不代表本公众号观点,我们不对其内容的准确性、真实性、合法性负责,也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版权属原作者,若侵犯到您的权益,请联系我们!
点击微信右上角的“+”,会出现“添加朋友”,进入“查找公众号”,输入“天下苏氏信息平台”或ID号“TXSS138”搜索,即可关注!查看历史消息请点击标题下面的“天下苏氏信息平台”进入,请大家分享本平台资讯,请订阅今日头条《天下苏氏信息平台》多谢!
![]()
![]() 阅不尽的历史、讲不完的精彩尽在阅读原文
阅不尽的历史、讲不完的精彩尽在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