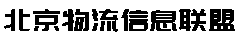
2022-04-25 10:12:11
本公众号由天津师范大学国际中国文学研究中心开发和更新维护,致力于介绍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历史和现状,发表海内外学者有关国际中国文学研究的最新学术成果。欢迎广大同仁踊跃赐稿,共同把这个公众号办好。来稿请发至邮箱gjzgwxyj@126.com。谢谢关注。
作者简介
高超,2012年毕业于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获文学博士学位,师从王晓平教授,现任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外国文学教研室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比较文学与海外汉学研究。
内容提要
本文以宇文所安《盛唐诗》及相关论文中对李白、杜甫诗作的分析为例,考察其中建构的诗人自我形象特点。李白、杜甫诗作中对诗人自我形象的塑造是“双重的”:一种形象是显现着的,另一种则是隐蔽在文本背后的。前者是一眼望去尽收眼底的形象,往往不一定是诗人真实的内心写照,而后者才是隐藏在表象后面的真实形象,它需要读者,尤其是智慧的读者通过思考挖掘出来。这种双重的自我形象构成了诗人“自我的完整映像”,它映射出了诗人精神世界的真实。
关键词
宇文所安;唐诗研究;自传诗;双重自我形象;李白;杜甫
宇文所安认为,中国古代诗人写的诗具有自传性质,因为自传只需“传达自己行为所包含的精神真实”[1],而“诗(这里仅仅是‘诗’,中文的诗)是内心生活的独特资料,是潜含着很强的自传性质的自我表现。由于它的特别的限定,诗成为内心生活的材料,成为一个人的‘志’,与‘情’或者主体的意向。”[2] 但是,自传诗中体现的作者的意向性,必须由读者的直觉与假设裁定,宇文所安据此分析了陶潜的诗作《归田园居》、《饮酒》,认为陶潜是他自己生活的搜集者与阐释者,诗中存在两个“自我”形象:一个是诗人预设的表面的“自我”角色呈现,一个则是掩藏在表面角色之下的复杂、真实的“自我”形象。前者是可传达的、确定的“自我”形象,而后者却是不确定的、复杂的,需要智性的读者方能透过表象、洞悉诗人隐秘的动机,建构其真实的诗人“自我”形象。这类对诗人双重自我形象的描摹与塑造的诗,被宇文所安称作“自传诗”,而陶潜也因此被宇文所安称为“中国第一位伟大的自传诗人”。[3]
注释
[1]参见宇文所安:《自我的完整映像——自传诗》,陈跃红、刘学慧译,载乐黛云、陈珏编选《北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名家十年文选》,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11页。
[2] 参见宇文所安:《自我的完整映像——自传诗》,陈跃红、刘学慧译,载乐黛云、陈珏编选《北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名家十年文选》,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12页。
[3]但他又认为,并不是所有的中国诗人都能称得上“自传诗人”这个称号,比如说公元前4世纪的大诗人屈原就不是,因为“对屈原作品的自传性说明依赖于文本与外部资料性传记之间的复杂的评注性调和”。 参见宇文所安:《自我的完整映像——自传诗》,陈跃红、刘学慧译,载乐黛云、陈珏编选《北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名家十年文选》,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35页注释⑿。
那么,作为读者又兼汉学家身份的宇文所安,是不是可以称得上他所指的智慧的读者呢?这是我们在其阐释唐诗的文本中,要格外关注的。在跨越中西文化的历史语境的大背景下,细读唐诗文本,建构唐代诗人形象,无疑符合比较文学形象学所称谓的“异域”、“他者”形象的制作特点。因之,从比较文学形象学视域出发,分析宇文所安所建构的唐代诗人形象特点,并与中国本土学者的研究相比照,辅助、参照相关历史文本,比较二者与历史真实的差异性,考察存在的误读、误释的现象,并探究其背后深层次的原因,不失为一个有趣的、富有比较文学意义的学术方向。
以下,我将以宇文所安《盛唐诗》及相关论文中对李白、杜甫诗作的分析为例,考察其中建构的诗人自我形象特点。
一、李白的形象
宇文所安认为,中国诗的开山纲领“诗言志”的内涵体现在两个层面上:一是把人心中的强烈感情、远大志向或者倏忽而来的情思都表达了出来;一是关注外部世界,但这只是在诗涉及观察者本人的复杂感受时。因此,“诗的焦点乃是诗人自我”。[4] 这样以来,阅读诗歌文本,就如同给诗人画像。
注释
[4] 参见宇文所安:《传统的叛逆》(为程章灿译自《传统的中国诗歌与诗论:世界的预言》第6章),载莫砺锋编《神女之探寻——英美学者论中国古典诗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211页。
宇文所安结合诗人李白的生平轶事,与李白诗作的自我形象塑造相呼应,勾勒出诗中呼之欲出的、直观的表面形象,比如,李白以少年游侠形象出场:“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5];李白的狂放饮士形象:“会须一饮三百杯”、“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6]。李白的率真放诞超越了同是来自蜀地的前辈陈子昂,也超越了西晋大诗人司马相如,因为贺知章赋予了他“谪仙人”的美誉,因之,李白从中“找到了能够具有仙人的特质,允许在诗歌和行为两个方面都狂放不羁。正如同后代批评家所称呼的那样,他是‘诗仙’,可以违反法则,因为他超越于法则之上……”[7]。“诗仙”与侠客、酒仙一样,拒绝按部就班、循规蹈矩,超越法则之上。
注释
[5] 宇文所安在叙述李白的青少年生活时,言称:“李白夸口在十几岁时擅长剑术,曾经杀死数人”参见《盛唐诗》,贾晋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2004年,第134页。所参应是李白《侠客行》中“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以及《与韩荆州书》中所言:“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
[6] 参见《全唐诗》(增订本)第3册卷一八二,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1684页。
[7]参见宇文所安:《盛唐诗》,贾晋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2004年,第136页。
“酒仙”的形象被后来的大诗人杜甫栩栩如生地描绘出来,“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杜甫《饮中八仙歌》)这个“斗酒诗百篇”的经典李白形象,千百年来为世人所公认而传颂,宇文所安认为它具有李白形象的基本成分:“纵吟不羁,放任自在,笑傲礼法;天赋仙姿,不同凡俗,行为特异,超越常规”[8],也就是说李白呈现出了丰富多样的面貌:狂饮者、狎、笑傲权贵和礼法的人,挥笔洒翰的诗人及自然率真的天才。宇文所安选用了殷璠《河岳英灵集》里选入的李白诗《山中问答》作为自我形象塑造成功的例子:“问余何意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窅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他认为,“殷璠对这首诗的选译,表明李白所创造的自我形象在天宝时是受到赏识的。如果李白与其他人的社会相隔离,他就会成为独立的仙人或桃花源中的居民。题目的问答并未发生,李白已经与世间俗人隔断联系,故没有社交活动。李白本人扮演了高适诗中不回答的渔夫角色。其他诗人可能会说曾经遇到这样一个人物,但李白却自称是这个人物。”[9] 也就是说,此篇诗中李白成功地塑造了一个隐逸的仙人形象。
宇文所安认为,上述李白诗中所建构的自我形象是表面角色的扮演,也许有真实的历史事实作为注脚,甚至我们可以找到丰富的轶事资料来书写李白作为“酒仙”与狂狷之士等特异性格和行为的诗人传奇,但那是李白的伪装,李白的预设的角色扮演:“他在诗中所扮演的各种角色——仙人、侠客、饮者及狂士,全部都是处于士大夫兼宁静隐士的双重角色之外的行为类型”[10],“像李白一类诗人的自我,是凭其狂放不羁的伪装来打动读者的。”[11] 诗作里浅层的表面角色扮演与伪装的形象,有时候也是历史的真实写照,因为李白长期漫游所获得的累累声誉,就是凭藉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形象:具有狂放性格的一个酒仙、隐士,而“李白作为‘逸人’的声誉,可以肯定是玄宗喜欢他的一个重要原因”[12]。但是,这种形象并不是李白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无论宫廷内外,李白的狂诞行为是其所选择的角色的组成部分;而不是如同某些传记作者所说的,是蔑视权位的真实表示。李白渴望被赏用,表示乐于进入宫廷,当他被迫离开时,发出了激烈的抱怨。狂野本是对他的期待,他并非有意地要对皇帝挑战。”[13]
注释
[8]参见宇文所安:《盛唐诗》,贾晋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2004年,第131页。
[9] 参见宇文所安:《盛唐诗》,贾晋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2004年,第160-161页。
[10]参见宇文所安:《盛唐诗》,贾晋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2004年,第160页。
[11]参见宇文所安:《传统的叛逆》(为程章灿译自《传统的中国诗歌与诗论:世界的预言》第6章),载莫砺锋编《神女之探寻——英美学者论中国古典诗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212页。
[12]宇文所安:《盛唐诗》,贾晋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2004年,第139页。
[13]宇文所安:《盛唐诗》,贾晋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2004年,第139页。
那么,掩藏在表面角色之下的那个复杂、真实的李白形象是什么样的呢?这个形象需要读者解读诗中作者所隐藏的个人的思绪和秘密来构建。宇文所安认为,李白的诗歌风格更是李白的天赋才情使然,“其目标是通过诗中的人物和隐蔽于诗歌后面的创造者,表现出一种独一无二的个性”[14],其诗中隐匿的这种个性形象才是李白复杂的、不确定的真实自我形象。
第一,部分诗作中的中心人物就是李白自己,李白在许多个人诗、甚至社交应景诗中占据着着诗歌舞台的中心,他通过自己的特立独行直接表现自我的个性中的那份率真与洒脱。宇文所安选取了李白的《夏日山中》、《自遣》等诗作为代表证明这一点:“他只写一个巨大的‘我’——我怎么样,我像什么,我说什么和做什么。他对外部世界几乎全不在意,除了可以放头巾的支挂物”——“懒摇白羽扇,裸袒青林中。脱巾挂石壁,露顶洒松风。”(《夏日山中》);还有《自遣》:对酒不觉暝,落花盈我衣。醉起步溪月,鸟还人亦稀。即便是饯别朋友的诗作《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叔云》,李白也当仁不让地抒发其别离时的狂热情绪,留下千古名句:“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销愁愁更愁”。[15]
第二,对“酒仙”李白形象的颠覆。宇文所安发现,酒是李白获得精神自由和直率行为的一种工具。[16] 换句话说,在世俗的世界里,李白常常借酒宣泄,举杯销愁,而在他自己打造的诗歌文本世界中:他俨然成为宇宙的主宰,自由精神的化身。宇文所安选译了《月下独酌》(四首之一):“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 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 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宇文所安认为,像这类诗作,李白关注的是饮者本人,而不是饮酒这件事,这就突出了诗人的自我形象,他说,“孤立既不是孤独,也不是宁静的隐逸,而是为了诗人提供了机会,显示创造性、丰富的自我,以及以自己的想象控制周围环境的能力。”[17] 酒在作者所创造的这个诗的世界中,成为了一个道具,成了邀明月相伴畅饮的一个由头。遗憾的事,宇文所安没有指出千古名句“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中所暗藏的典故,也失去一次更好地解密李白隐匿情思的机会。我们知道,陶潜《杂诗》有言:“欲言无余和,挥杯劝孤影。”此处用典,使得诗歌文本中的世界,穿越了陶潜的时代,把陶潜的身世与诗人置放在一起加以比照。显然,陶渊明的思绪是凄凉孤独的,尤其从紧接着的结尾两句“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更能看出陶渊明的悲观绝望之情,但是与陶潜一样怀才见弃的李白,精神境界恰恰与之形成鲜明的对照:化身为自由的精灵,热情地邀请高洁的明月相伴畅饮、歌舞,而且“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是多大的气魄和胸襟。胸怀宇宙的大诗人对人的渺小卑微看得很清楚,尽管诗中对俗世间的悲欢离合他一字不提,却自然包容天地万物,即便陈子昂的“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也不及也。我们既没有必要抬高李白,说他是怀有积极的乐观主义思想,也没有必要贬抑李白,说他宣扬及时行乐的消极、颓废思想。在《传统的叛逆》一文中,宇文所安细致入微地揭示了酒在李白诗中所起的作用,似可以放在此处作为“脚注”的。他说,“据说李白有过这么一句妙语:‘酒以成礼’。酒使我们敢于破坏礼法,为所欲为——心若古井或是狂似暴君,抑郁不乐或是欢呼雀跃。在举杯欲饮的短暂的一瞬间,酒便揭示了约束社会存在的那些陈规陋习的无聊。再多喝一些,酒甚至会使我们意识到生命的限制也是可笑的,并产生一种如醉的幻觉,以为我们可以摆脱自然的束缚……无拘无束的意志仿佛是一种醉酒状态。”[18] 酒,掩饰了诗人个性中孤高飘逸的个性,同时,也宣告了诗人对世俗传统与诗歌传统的双重叛逆。
注释
[14] 宇文所安:《盛唐诗》,贾晋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2004年,第131页。
[15]宇文所安:《盛唐诗》,贾晋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2004年,第161-162页。
[16]宇文所安:《盛唐诗》,贾晋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2004年,第162页。
[17]宇文所安:《盛唐诗》,贾晋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2004年,第163页。
[18] 参见宇文所安:《传统的叛逆》(为程章灿译自《传统的中国诗歌与诗论:世界的预言》第6章),载莫砺锋编《神女之探寻——英美学者论中国古典诗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218-219页。
宇文所安认为,李白孤高狂傲,但并不孤独,在诗歌文本中非常充分地显示出这种自我的特点。[19] 他同样持这种观点解读《独坐敬亭山》:“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20] 宇文所安认为,“如果鸟和云离开了他,他能够找到更可靠的伙伴。在诗歌想象中,诗人能够想入非非,任意地构造和理解世界。”[21] 诗歌,无论中外,总是时不时地充满了隐喻。如果宇文所安仅仅从字面的表层意义解释这首诗,可能会忽略它隐含的本意。这里,我们参照近代著名学者、诗人俞陛云[22](1868-1950)先生对作者本意的索解来加以比照:“前二句以云鸟为喻,言众人皆高取功名,而已独翛然自远。后二句以山为喻,言世既与我相遗,惟敬亭山色,我不厌看,山亦爱我。夫青山漠漠无情,焉知憎爱,而言不厌我者,乃太白愤世之深,愿遗世独立,索知音于无情之物也。”[23] 比较宇文所安与俞碧云二人对《独坐敬亭山》的阐释,我们发现,两种释读都含有李白孤高狂傲的一面,但后者更深入一层,更贴切诗作的内涵,否则,诗作不免流于贫乏肤浅。
注释
[19]宇文所安:《盛唐诗》,贾晋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2004年,第163页。
[20]参见《全唐诗》(增订本)第3册卷一八二,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1864页。
[21]宇文所安:《盛唐诗》,贾晋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2004年,第163页。
[22] 清末经学大师俞樾之孙,现代文学家俞平伯之父,著有《小竹里馆吟草》、《乐青词》、《诗境浅说》、《诗境浅说续》、《唐五代两宋词选释》、《清代闺秀诗话》等。
[23] 俞陛云:《诗境浅说》,北京: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出版社,2011年,第117页。
第三,对“逸士”形象的颠覆。宇文所安认为,以道教题材入诗,表现了李白对道教的熟悉,但是这可能是李白的入世的策略,试图借朝廷对道教的尊崇而走这条终南山捷径。“与王维相比,李白更算不上是宗教诗人:他所深切关注的,既不是道家的宇宙法则,也不是道教炼丹术的原始科学。对于李白来说,神仙不过是驰骋幻想的对象和释放想象力的工具。”[24] 比如,在《元丹邱歌》中有言:“身骑飞龙耳生风,横河跨海与天通。我知尔游心无穷。”
此外,宇文所安在《盛唐诗》中还提到,诗人早年曾作《大鹏赋》,以“大鹏”自喻,向世人宣告了青年李白的宏大抱负,而李白临终作诗《临路歌》:“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余风激兮万世,游扶桑兮挂石袂。后人得之传此,仲尼亡兮谁为出涕?”,依然以大鹏自比。大鹏作为诗人的隐喻,贯穿了李白的一生,所以,李白平生的豪情壮志从中可以看得很清楚。这也是颠覆李白表面上的“逸士”形象的一个极佳例证。李白以“大鹏”自比的还有早年诗作《上李邕》:“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世人见我恒殊调,闻余大言皆冷笑。宣父犹能畏后生,丈夫未可轻年少。”宇文所安未提及的这首诗同样可以佐证李白以“伟大的自我”形象出现,远非道家的“仙人”、“逸士”形象。
注释
[24]宇文所安:《盛唐诗》,贾晋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2004年,第165页。
第四,诗作中描绘的人物,实质上是对李白情思的隐喻。比如,宇文所安在《盛唐诗》中译介了李白的两首咏史题材的《古风》,一首是:“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明断自天启,大略驾群才。收兵铸金人,函谷正东开。铭功会稽岭,聘望琅邪台。刑徒七十万,起土骊山隈。尚采不死药,茫然使心哀。连弩射海鱼,长鲸正崔嵬。额鼻象五岳,扬波喷云雷。鬐鬣蔽青天,何由睹蓬莱。徐市载秦女,楼船几时回?但见三泉下,金棺葬寒灰。”一首是:“秦皇按宝剑,赫怒震威神。逐日巡海右,驱石驾沧津。征卒空九宇,作桥伤万人。但求蓬岛药,岂思农扈春。力尽功不赡,千载为悲辛。”两首《古风》主题的批判与讽刺意味比较明显,但是宇文所安却读出了别样意味:“但是没有读者会忽略李白对秦始皇神奇形象的真实迷恋,这一点胜过任何时事解释”[25]。“在最佳状态下,李白通常写的是他最喜爱的对象——李白。”[26] 因之,尽管题材上沿袭了陈子昂《感遇》诗的传统,是以建安、魏晋风格写成的复古诗,但复古的背后却有着李白自身的影子。
最后,李白是以写自己著称,但有的诗作中完全失去了他自己,无影无踪,比如,李白写的怀古诗,读者看到的全是栩栩如生的古代人物画面的一幕一幕,里面没有作者的任何声音,不像有的诗人如杜牧在历史的景象中插进作者对历史人物、事件的评议。即便如此,宇文所安认为,这同样是在写他自己。一是由怀古诗这种文体所决定的,因为“怀古诗可能确实包含一些推测的诗句,设想古迹过去曾经有的风貌,但诗歌中心不可避免地是诗人的现在:他所看到的,所感受到的,以及(将想象行为降低至思考过程)所想像到的”[27];一是由李白独特的个性所决定的,“这位付出如此多的精力以创造诗歌自我形象的诗人,也能将自己从通常要求个人反应的诗中完全退出。这似乎是自相矛盾的,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创造自我的力量中,隐含着否定自我的力量,这一点是王维所做不到的。正由于李白缺乏京城诗人对真实的追求,他才能驰骋虚构想象,从眼前的世界及作为补充的个人反应中解放出来。”[28]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宇文所安通过对李白诗作的解读建构了李白“双重自我形象”的特点:一是李白在苏颋、贺知章等著名诗人的鼓励下,“找到了能够顺当容纳其蜀地角色的观念:他具有仙人的特质,允许在诗歌和行为两方面都狂放不羁”[29],因此在其诗作中“呈现出了丰富多样的面貌:狂饮者,狎,笑傲权贵和礼法的人,挥笔洒翰的诗人,及自然率真的天才”[30],这种自我形象属于李白预设的表面的“自我”角色呈现,是一种伪装的“自我”形象,是诗作直接传达给读者的确定的“自我”形象;而另一个真实的“自我”形象除却其真实率真的个性以及与其预设的表面的“自我”形象相矛盾的一面之外,更多地指向前者的反面。
注释
[25]宇文所安.盛唐诗[M].贾晋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2004.158.
[26]宇文所安.盛唐诗[M].贾晋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2004.156.
[27]宇文所安.盛唐诗[M].贾晋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2004.145.
[28]宇文所安.盛唐诗[M].贾晋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2004.164.
[29]宇文所安.盛唐诗[M].贾晋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2004.136.
[30]宇文所安.盛唐诗[M].贾晋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2004.136.
二、杜甫的形象
宇文所安对杜甫的评价超过了李白,他认为杜甫是最伟大的中国诗人,“在中国诗歌传统中,杜甫几乎超越了评判,,他的文学成就本身已成为文学标准的历史构成的一个重要部分。”[31] 在宇文所安眼里,杜甫是一个诗人,他的伟大之处在于他的诗作呈现出复杂多样性的特点,“杜甫是律诗的文体大师,社会批评的诗人,自我表现的诗人,幽默随便的智者,帝国秩序的颂扬者,日常生活的诗人,及虚幻想象的诗人。”[32] 就是因为诗人个性的复杂多样,宇文所安觉得无法对杜甫做出整体上的评价——“文学史的功用之一是指出诗人的特性,但杜甫的诗歌拒绝了这种评价,他的作品只有一个方面可以从整体强调而不致被曲解,这就是它的复杂多样。”[33] 因此,杜诗的这种复杂多样性特点,就成为宇文所安书写杜诗史要表现的最重要内容。然而,宇文所安的《盛唐诗》本来就不以材料的丰富性见长,而短短的一个章节更无法容纳对杜诗的复杂多样性特点的阐释。所以,这里就必然衍生了一个矛盾,而且是自相矛盾——即宇文所安对杜诗的阐释不得不陷入了一种简单的概括:而这一直以来是他极力反对的。我们仅仅从一个方面可以看出上述这一点:宇文所安选取分析的杜诗数目异常少,他只选取在作者创作的某个历史阶段最出色、最有代表性的诗作,有的限于长度而只能截取其中的一段。
这里,我们主要撷取宇文所安所集中关注的“自我表现”——即对自我形象塑造的所谓“自传诗”,材料主要集中在《盛唐诗》第十一章以及《自我的完整映像——自传诗》[34]一文中的杜诗分析。
杜诗历来被视作“诗史”,因为杜甫擅长以诗的形式来写历史,“甫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35] 这一点宇文所安在《盛唐诗》中有类似的重述——“特定时代的真实个人‘历史’……杜甫的许多诗篇无需涉及传记或历史背景就能读懂,,其契合程度远远超过大多数同时代诗人的作品。,特别是与安禄山叛乱中事件的契合,使杜甫赢得了‘诗史’的称号”[36]。因此,杜甫诗作的写实性为建构、描摹杜甫形象提供了一个准确性很高的参照文本。下面,我们来观察宇文氏所撷取的杜诗材料及其具体的阐释。
注释
[31]宇文所安.盛唐诗[M].贾晋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2004.209.
[32]宇文所安.盛唐诗[M].贾晋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2004.210.
[33]宇文所安.盛唐诗[M].贾晋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2004.210.
[34]参见宇文所安:《自我的完整映像——自传诗》,陈跃红、刘学慧译,载乐黛云、陈珏编选《北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名家十年文选》,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10-137页。
[35] 参见[北宋]欧阳修:《新唐书》卷第一百九十二,列传第一百二十六“文艺上”。
[36]宇文所安:《盛唐诗》,贾晋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2004年,第212页。
首先,宇文所安发现,杜甫对自我形象的关注并不亚于李白。杜甫早期的“自画像”源于他的《壮游》一诗:“往昔十四五,出游翰墨场。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扬。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性豪业嗜酒,嫉恶怀刚肠。脱略小时辈,结交皆老苍。饮酣视八极,俗物都茫茫……”。对于杜甫这样一首自传性极强的诗,宇文所安认为,这是杜甫为了为了渴望声名流传后世而作。[37] 这也是宇文所安认为自传诗的目的之所在。[38] 杜甫的自传诗是杜甫对自我的认识,对自我形象的建构,它有一定的功利性:那就是为了渴望声名流播后世。宇文所安对这首诗并没有做过多的分析,可能是因为他认为这是诗人建构的双重自我形象的第一种——诗人预设的表面的“自我”角色呈现,是可传达的、确定的“自我”形象。一般读者都可以看得出,这首诗中呈现出来的呼之欲出的杜甫形象:一个天赋才情、豪气逼人的狂士形象。有学者认为,这种“自我的积极评价”是我国文学的传统,“即使是杜甫也多‘豪迈’的自我肯定”。[39]
注释
[37]宇文所安说,“诗人后来自称是神童,……他无疑希望这一传记惯例将充分引起他的后代传记家的注意(后来确实如此)……那些未来的传记家是帮助他获得所渴求的后代声名的必不可少人物。” 宇文所安:《盛唐诗》,贾晋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2004年,第213页。
[38] 宇文所安在《自我的完整映像——自传诗》开篇引用曹丕《论文》中的一句话,“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幅,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参见宇文所安:《自我的完整映像——自传诗》,陈跃红、刘学慧译,载乐黛云、陈珏编选《北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名家十年文选》,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10页。
[39] 详见陆建德:《自我的风景》,载《外国文学评论》,2011年第4期,第194页。
宇文所安还选译了《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他摘录了开头的一段文字:“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居然成濩落,白首甘契阔。盖棺事则已,此志常觊豁。”[40] 他认为,“诗篇开始于自我嘲讽和自负傲气的奇妙混合,这种混合后来成为杜甫自我形象的特征”(The poem begins with the curious mixture of self-mockery and assertive pride that was to become characteristic of Tu Fu's self-image. [41] )“散漫的自我分析在中国诗歌中有其先例,但杜甫的复杂陈述——结合嘲讽、严肃及辛酸,反映了一种矛盾和深度,没有一位前此的诗人能够匹敌。”[42] 宇文所安解释得很抽象,认为“自我嘲讽和自负傲气的奇妙混合”是杜甫自我形象的特征,而且因为分析“反映了一种深度和矛盾 ”所以“没有一位前此的诗人能够匹敌”,尽管这种分析是“散漫的自我分析”。自嘲的因素是有的,因为杜甫作此诗是天宝十四年(755)年,已45岁了,这把年纪还是一介平民,“居然成濩落”般地一事无成,却依然怀抱着“窃比稷与契”的理想,所以说自己“拙”与“愚”。但是,“自负傲气”与“散漫的分析”是没有的,因为杜甫说自己“拙”与“愚”是自谦的说法,略有自嘲的成分,但说得很诚恳,只是为了表达对“致君尧舜”、“窃比稷契”的理想坚守,并且与后面的“白首甘契阔”、“盖棺事则已,此志常觊豁”同声呼应,前后连贯。诗语完全发自杜甫肺腑,表达了杜甫坦率、真诚的信念与情感。“诗篇的前三十二句是扩大的独白,诗人在其中与自己争论,为自己不管反复失败而坚持求仕的行为辩护。”(The first thirty-two lines of the poem are an extended monologue in which the poet argues with himself and defends his continuing search for offìce despite repeated failures.[43])宇文所安说杜甫为求官的屡败屡战而辩护,其实未能深解上述杜甫“窃比稷与契”的胸怀,绝非一般儒生追求功名利禄之俗念。此处暗含一典:即《孟子·离娄下》:“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另有《杜臆》解释得更明白:“人多疑自许稷、契之语,不知稷、契无他奇,惟此己饥己溺之念而已。”[44] 叶嘉莹先生在讲解“窃比稷与契”这句诗的时候,说了一句非常中肯的话,她说,“诗人常常浪漫多情,写爱情诗可以写得真切动人,这并不奇怪。而杜甫之所以难得,就在于他把诗人的感情与伦理道德合一了。杜甫的感情很真诚……他能够把他对于国家人民的爱写得那样真诚,以一种像别人对爱情那样深挚的感情来爱他的国家和民族,这是杜甫之所以为‘诗圣’的一个重要原因”。[45] 而且诗中明言“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葵藿倾太阳,物性固难夺”,则是进一步表达自己济世救民的热忱与志向,并且讥讽那些“顾惟蝼蚁辈,但自求其穴”的自私自利。因此,这前三十二句的确是杜甫的内心独白,但绝不是为他求官作辩护。因为宇文所安作如是观,所以导致了他对诗的主题的误读——“主题的微妙延续(诗人希望像后稷和契一样,成为伟大家族的创立者,而后来却是其子的死亡)——subtle resumptions of themes (the poet's longing to be, like Hou Chi and Chieh, the founder of a great line, and later, the death of his child” )[46] 治唐诗研究学者莫砺锋先生在为《盛唐诗》写书评时,也细心地指出了这一点,“通读全诗,杜甫何尝有丝毫要创立‘伟大家族’的意思?”[47] 的确,杜甫这首诗以回家探亲的时间顺序为叙述线索,对沿途见闻以及归家后情景做了近乎实录的描绘,同时前后穿插咏怀抒情、议论的内容,真实自然地表现了诗人“穷年忧黎元”的悲天悯人、关怀现世的伟大情怀。显然,如果从描画诗人杜甫的自我形象这个角度而言,宇文所安对这首诗的误读可能会影响他理解“诗圣”之所以是“诗圣”的内在原因——杜甫已经超越了一般儒生“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思想。
注释
[40] 参见《全唐诗》(增订本)第4册卷二一六,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2266页。
[41] Stephen Owen, The Great Age of Chinese Poetry: the High T`ang. New Haven: Yale, 1980, p195.
[42]宇文所安:《盛唐诗》,贾晋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2004年,第212页。原句为:Discursive self-analysis did have its antecedents in Chinese poetry,but the complexity of Tu Fu's statement一its combination of mockery,grandeur,and bitterness-reflect an ambivalence and depth that no earlier poet could match.参见原著Stephen Owen, The Great Age of Chinese Poetry: the High T`ang. New Haven: Yale, 1980, p195.
[43]参见原著Stephen Owen, The Great Age of Chinese Poetry: the High T`ang. New Haven: Yale, 1980, p195.
[44] 转引自莫砺锋:《<初唐诗>与<盛唐诗>》,《唐研究》(第二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490页。
[45] 叶嘉莹:《叶嘉莹说杜甫诗》,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66页。
[46] Stephen Owen, The Great Age of Chinese Poetry: the High T`ang. New Haven: Yale, 1980, p197.
[47]莫砺锋:《<初唐诗>与<盛唐诗>》,《唐研究》(第二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491页。
宇文所安发现,杜甫漂泊成都时的诗作体现了杜甫的一种“作为老人的成熟的、半幽默的自我形象”[48]。他把《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组诗之二作为这一自我形象的著名范例。原诗句如下:“稠花乱蕊畏江滨,行步欹危实怕春。诗酒尚堪驱使在,未须料理白头人。”[49] 宇文所安体味此诗时发现,这首诗可以引起两种情绪——“幽默感或畏惧感”[50] ,这两种情绪都是杜甫心理的真实写照:一是由于年纪太大而“畏江滨”、“ 实怕春”;一是还不复老:“诗酒尚堪驱使在”。可贵的一点是,宇文所安发现杜甫观察自己的角度充满睿智,他不完全是自己审视自己,还站在他人的视点上观察自己,故而怀着“畏惧里带着幽默地观查自己”[51]——并且自言自语地,抑或是对着后世子孙言说“未须料理白头人”。
宇文所安认为,“诗歌的本质成为杜甫自我形象的一部分”[52],他引用了杜甫的诗句“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老去诗篇浑漫兴。”作为例证。他进一步指出,“这些诗句的轻松、通俗语调是杜甫成都时期诗篇的特色,嘲讽地反射了狂士的自我形象”[53] 也就是说,宇文所安认为,杜甫骨子里具有文人的“狂放”本性, 而这种狂放就是往日“诗酒尚堪驱使在”的“诗酒人生”,只不过这诗与酒之间的权重一定是落在他的“诗”上——换句话说,杜甫的形象活在他的诗里,那么,宇文所安《自传诗》开篇引用曹丕的那句“寄身于翰墨”[54] 的话可以放在这里作为注解。
注释
[48]原句为:“Perhaps the most characteristic stance of the Ch'eng-tu poems is a mellow,half-humorous vision of himself as an old man.”参见Stephen Owen, The Great Age of Chinese Poetry: the High T`ang. New Haven: Yale, 1980, p207.
[49]参见《全唐诗》(增订本)第4册卷二一六,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2453页。
[50]原句为:“The poem may be read with humor or with terror”,参见Stephen Owen, The Great Age of Chinese Poetry: the High T`ang. New Haven: Yale, 1980, p207.
[51]原句:“observe himself with wry horror”,参见Stephen Owen, The Great Age of Chinese Poetry: the High T`ang. New Haven: Yale, 1980, p207.
[52] 原句:“the poetic nature becomes part of Tu Fu's self-image ”, 参见Stephen Owen, The Great Age of Chinese Poetry: the High T`ang. New Haven: Yale, 1980, p209.
[53]原文为:“The easygoing,colloquial tone of these line was characteristic of Tu Fu's Ch’eng-tu years and mockingly reflected the self-image of the eccentric.”参见Stephen Owen, The Great Age of Chinese Poetry: the High T`ang. New Haven: Yale, 1980, p209.
[54] “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幅,不假良吏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曹丕《论文》)参见宇文所安:《自我的完整映像——自传诗》,陈跃红、刘学慧译,载乐黛云、陈珏编选《北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名家十年文选》,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10页。
《自传诗》一文是以杜甫诗作为主要范例的,其中宇文所安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在中国诗歌传统中,杜诗是最出色也最艰涩的自传诗。”[55] 作为例证而特别提出进行分析的是《空囊》一诗:“翠柏苦犹食,明霞高可餐。世人共鲁莽,吾道属艰难。不爨井晨冻,无衣床夜寒。囊空恐羞涩,留得一钱看。”一般而言,《空囊》并不难解,但宇文所安却细读文本、大量分析之后,告诉我们它很艰涩,因为“杜甫诗中的‘人’格外复杂:奇怪的是,在双重虚构中却出现一个坦诚、真实的声音——一个虚构告诉我们他的口袋是空的,一个虚构又告诉我们他的口袋并不空。杜甫是聪明的自传者,他穿越了属于非智慧的、仅仅是人类自我的欺骗性外表。”[56] “囊空恐羞涩,留得一钱看”的辛酸与幽默,完全是杜甫自己处境的真实写照,是杜甫“含泪的笑”。如果作为那个“作为老人的成熟的、半幽默的自我形象”的例证,《空囊》这首诗还是比较合适的。但是,宇文所安如果依此得出下面的结论,肯定存在过度阐释之嫌。“如果我们看到一个写自己的诗人自信地暴露人与角色的张力——他不仅表现他期望的自我形象,并且以智者的锐目看穿它;在某一意义上说,这是一个有着普通人的希望和幻想的日常人——可能比智者更有诗趣,但并不那么伟大。在另一个意义上,这也是一个智者,透过角色看到动机和渴望,揭示一个人(恰巧是他自己)所希望表现的东西以外的东西。不可否认,这是一种自相矛盾的立场,但其主导声音得到了智者诚实而清晰的保证。”[57]
此外,宇文所安还提出一个“他者自我(self other)”的概念,认为“这里诗人把一个他者看作自我……杜甫之所以‘看透’他的角色就是从外向里注视这样一个‘他者自我’。这一过程的第一步比喻: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58] “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源自杜甫的《旅夜书怀》,是他离开成都后所作。宇文所安认为,杜甫离开成都之后的诗日益与自我有关,“在沿长江而下时他转向‘我似什么’的问题,并反复从大江的各种形态和生物中寻求答案”。[59] 宇文所安还引用了杜诗《江汉》作为例证:“江汉思归客,乾坤一腐儒。片云天共远,永夜月同孤。落日心犹壮,秋风病欲苏。古来存老马,不必取长途。”《旅夜书怀》中的“一沙鸥”与《江汉》中的“一腐儒”都是在一定距离上被观照的‘他者自我’形象,宇文所安认为,在这些诗作中“诗人不再宣称知道他是谁,而在思想和外部世界中寻找一个形象以回答‘何所似’的问题”。[60] 的确,独立在茫茫宇宙中,不少诗人都在思考着同样一个问题:“我是谁?”,从“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陈子昂,到“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的李白,再到“江汉思归客,乾坤一腐儒”的杜甫,也许杜甫的名句“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可以作为他们的共同回答,因为“我是谁?”、“他是谁?”、“谁是我?”类似这样问题的答案全都包容在这一句富有哲理内涵的诗句中。
注释
[55]参见宇文所安:《自我的完整映像——自传诗》,陈跃红、刘学慧译,载乐黛云、陈珏编选《北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名家十年文选》,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29页。
[56]参见宇文所安:《自我的完整映像——自传诗》,陈跃红、刘学慧译,载乐黛云、陈珏编选《北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名家十年文选》,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25页。
[57]参见宇文所安:《自我的完整映像——自传诗》,陈跃红、刘学慧译,载乐黛云、陈珏编选《北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名家十年文选》,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24页。
[58]参见宇文所安:《自我的完整映像——自传诗》,陈跃红、刘学慧译,载乐黛云、陈珏编选《北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名家十年文选》,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29页。
[59]宇文所安:《盛唐诗》,贾晋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2004年,第240页。
我认为,上述宇文所安所指的“艰涩”是就杜甫诗中所蕴含的哲理性思考而言,换言之,杜甫的形象中葆有一种诗化的哲人形象特点。这种通过诗中所蕴含的诗人自我形象的解读,而抵达诗歌文本隐含的深刻主题,是一种令人欣喜的发现与创新。因为对类似上述诗歌的解读,还存在着另外一种方式,即以诗句背后的隐喻来索解唐诗所蕴含的主旨。类似于“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这样的诗句,字面的诗义异常清晰,而且瞬间从脑际映入眼帘的更是异常清晰的视觉画面,不过,但凡读者再深入一层,思索其字面意义之外是否还有其他深意时,这时就涉及到对隐喻的语言的索解了。这可能就是哈罗德·布罗姆(Harold Bloom)想交给我们“读诗的艺术”的动因了。这里我们只想征引他的一句话,“诗本质上是比喻性的语言,集中凝练故其形式兼具表现力和启示性。比喻是对字面意义的一种偏离,而一首伟大的诗的形式自身就可以是一种修辞(转换)或比喻。‘比喻性的语言’在字典上常被等同于‘隐喻性的语言’,但隐喻实际上是一种高度特指的比喻(或对字面意义的转换)。”[61] 由是观之,中西诗歌在语言的隐喻层面上存在的共性也是很明显的。我们先避开西方文艺评论家在比喻修辞的复杂分类的描述,直奔如何索解隐喻背后所蕴含的主旨问题。这种解析的方式,尤其用来索解唐诗意蕴的方式,是由美籍美国华裔学者高友工、梅祖麟两位先生完成的。他们在《唐诗的意蕴、隐喻和典故》一文中,指出,绝大多数的隐喻是通过语意的相似性而“相互发明”——形成对等关系,以及相互对照——形成对比关系,而且相似性与对比性是并存的。这种对等、对比关系的形成,通过隐喻的构成而产生新的意蕴。比如,李白《送友人》诗句:“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浮云”和“落日”都具有两层意思,即字面的和隐喻的:游子的漂泊不定,无忧无虑,有如浮云,而朋友的离别与日之将落则触发同样的失落感。高、美二位先生所举的第二个例子,就是上述宇文所安阐释杜甫的“双重自我形象”的例子:杜甫诗句“江汉思归客,乾坤一腐儒”中的对比关系比对等关系要强烈些,“人影的渺小与宇宙的浩大相互对照。对照同样也能够创生出新的意蕴;渺小并非‘思归客’或‘腐儒’本身所固有的特质,但是当他们出现在两条大河(‘江汉’)和天地之象征(‘乾坤’)这样一种广阔无垠的客体而前的时候,便产生了这样一种特殊语意。”[62] 上述高、梅二位学者通过诗句的隐喻来索解意蕴,可与宇文所安对诗歌的阐释方式相互比照,尽管他们的侧重点不一样,但得到的意蕴主旨却基本相同,宇文所安在构建诗歌文本里的人物形象最本真的特点时,势必借鉴了前者的索解方式或者说是以前者的索解方式为基础的。
注释
[60]参见宇文所安:《自我的完整映像——自传诗》,陈跃红、刘学慧译,载乐黛云、陈珏编选《北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名家十年文选》,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29页。
[61] [美]哈罗德·布罗姆 等著:《读诗的艺术》,王敖 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页。
[62] [美] 高友工,梅祖麟著《唐诗的意蕴、隐喻与典故》,孙乃修译,载周发祥.中外比较文学译文集[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 185-186.
三、显现与隐蔽:凸显诗人精神世界的真实
上述对李、杜诗中“双重自我形象”的解读,是宇文所安的新发现。不难看出,这“发现”背后显然受到接受美学思想的启发,文本中的“双重自我形象”都是文本世界的创造者与读者共同建构的:一种形象是显现着的,另一种则是隐蔽在文本背后的。前者是一眼望去尽收眼底的形象,往往不一定是诗人真实的内心写照,而后者才是隐藏在表象后面的真实形象,它需要读者,尤其是智慧的读者通过思考挖掘出来。
唐诗文本世界里所呈现的诗人自我形象,其本身只不过是诗作者的“自画像”,犹如上帝造人一般,是上帝根据自己的模样塑造出来的,而究其实质,它仍然是一种文学的虚构,是诗作者依据自身现实生活的经验,运用“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最后诉诸语言的一种艺术创造,同时,反过来又反映现实语境中诗作者的一种真实境况——这种“真实”即是宇文所安所言称的“内心生活的独特的资料”[63],而身为诗歌文本世界的创造者的诗人,则是“那些传达自己行为所包含的精神真实的人”[64]。宇文所安所言称的“自传诗”——“自我的完整映像”,即是诗人的“双重自我形象”,它映射出了诗人精神世界的真实。
注释
[63] 宇文所安:《自我的完整映像——自传诗》,陈跃红、刘学慧译,载乐黛云、陈珏编选《北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名家十年文选》,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12页。
[64]宇文所安:《自我的完整映像——自传诗》,陈跃红、刘学慧译,载乐黛云、陈珏编选《北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名家十年文选》,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11页。
本文发表于《汉学研究》第十五集。北京:学苑出版社2013年版,第190-202页。
-国际中国文学研究-
图文编辑:李盟
喜欢请记得点赞哦!
相关推荐
友情链接
Copyright © 2023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北京物流信息联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