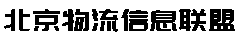--- Tips:点击上方蓝色【大家】 查看往期精彩内容---
“光说自己好话的人,可能是在撒谎,因为任何人的生命,如果从其内部观察,都不外乎一系列的失败。”——奥威尔
▍ 一
达利的一批作品正在上海的两个展览馆同时展出,真迹夹杂在高仿品之间。近距离看到那张地球人都认识的脸,忽然觉得它如此陌生:那上面长了一团让人难以捉摸的表情——困惑?惊奇?冷漠?窃喜?孤傲?失望?嗔怒?说不清。想一想与达利同级别或同时代的其他文化名人:他认识的大画家毕加索,设计天才可可·香奈儿,电影导演布努艾尔,诗人加西亚·洛尔卡,都是大艺术家,可无论哪个人的照片,都不像达利那样,那么不真实,那么拒人千里之外,那么缺少真实的性情。
篇首所引的奥威尔语,出自其短文“萨尔瓦多·达利札记”的开头。该文作于1944年,达利正在美国避战,享受着其自传《萨尔瓦多·达利的秘密生活》的出版引发的轰轰热炒。单看书名,他就像是写了一本本该由别人给他写的传记似的,没等别人起底,就抢先自曝。从1920年代末以来,他的名气和地位就青云直上,出一本暴露个人隐私的自传绝对能造福出版商,但奥威尔指出,书中的细节肯定有很多不实,达利脑洞大,想象力惊人,惯于夸大、扭曲、偏移、变形,他把这技术用到了自传写作之中——所以他撒谎了。
但奥威尔随即又说:“即使最不诚实的自传……也可能在无意间暴露出传主真实的一面” ——就好比说,你戴着手套去打开一扇别人家的房门也会留下痕迹,歪曲的痕迹。
达利撒了哪些谎,又暴露了怎样的真实?
▲资料图:达利
简单来说,达利以夸大的方式讲了他童年以来做过的各种古怪惊悚的事情:踢妹妹的脑袋,把别的孩子从大桥上推下去,咬一只蝙蝠,挖死驴的眼珠,跟未来的妻子加拉初次亲吻时耸动的交锋——
我把加拉的头推到后面,再拽着头发拉回来;我歇斯底里地颤抖着,命令她:
“现在,告诉我你想让我对你做什么!不过要慢慢地说,看着我的眼睛,用最下流、最、最能是我俩感到羞耻的词句!”
加拉的表情,由愉快一变而成为专横,回答说:
“我想要你杀了我!”
这是真的吗?看多了达利的作品,你就相信他在真实生活中就是这么乖戾。不但有暴力倾向,而且达利还是个“嗜痂成癖”之人:恋尸、恋血、窥淫、性倒错、食屎……他在自传里坦陈了自己的重口味:他画《大狂》,他也坦陈自己成性,他画《窥淫者》,他也确实喜欢窥看他人行淫,晚年他们夫妇住在自己的城堡里,有专人输送男女名模过去,特别是长有女人态的男人,供他“观看”。
奥威尔1950年就死了,年仅47岁,而达利和他差不多同龄,活到了1989年,奥威尔不知道,达利的《出租车里的腐烂女模特》一画中的意象,后来也真实发生在了达利本人身上。那是1982年6月10日,他的妻子加拉去世于巴塞罗那,达利想把她迁回到他们的城堡普勃尔,但他自恋成性,从来不肯走任何正规程序,也不懂那些。他把加拉放在自己的凯迪拉克车后座上,安排一名女护士守在旁边,一路开了回去。晚年的达利实现了他画画时的梦想:车里的女尸,只不过他雇了巴城当地的医生给加拉抹上香油,没让尸体半路就腐烂。
▍ 二
对达利的“怪癖”、“恶癖”,如果去掉道德谴责的感情色彩,可以说,他是先给自己叠加许多“身份”,然后把它们落实在画布上。他想做很多人:六岁时想做厨师,;他想做天才,想做疯子,想做怪物,想做野兽,想做自我阉割者,也许还想做一个埋头吃粪的人,当他着手画出自己梦想要成为的样子时,他就模糊掉了生活和艺术、虚构和现实之间的界线:不管在画布上扭曲的人形里,还是在现实的血肉之躯中,他都是上述所有的身份。
让奥威尔感到不舒服的,首先是这种蓄意的模糊,其次才是屎尿、粪便、肮脏的肉体、瘫软的钟、各种粘糊糊的不明物体、窥淫、暴力、阉割,等等诸如此类的主题所引发的强烈恶心感。他写道:
“(达利自传中)记录的一些事情,一看就不可信;而另一些事情,或者被重新编排过,或者被美化,日常生活中那些丢人的事、平常的事,都被去掉了。就连达利都认为自己是个自恋狂,而他的自传,不过是粉红色聚光灯下的表演。”
他说的“一看就不可信”的事,是指那些太破下限、太没节操的细节,一些耸人听闻的事情。比如说,三十年前,某人被灌醉后醒来发现丢了一个肾,肯定是假新闻,但如今我们都笃信有加,还会互相提醒,因为我们对世道之黑暗程度的认知早已更新过了;奥威尔也不能相信这种事情会是真的:孩提时代的达利,一日得到一只翅膀受伤的蝙蝠,给它做了一个临时小屋放进去,第二天他去看蝙蝠,大吃一惊,蝙蝠已经半死不活,许多蚂蚁占领了它的身体:
突然我做了一件不可理解的行为……我迅速捡起了浑身蚂蚁的蝙蝠,把它举到嘴边,我伤心得无以复加,但没有像预想的那样亲吻它,而是用我的上下颚给了它狠狠的一口,好像都快把它咬成两半了。我带着强烈的恶心感把它扔到了洗衣房,逃之夭夭。
崇拜达利的人,会怎么看这件记载的真实性?单是想想那个画面就够头皮发麻的了。对奥威尔来说,它太不可思议,太不可理喻,而达利的文字又炫目而夸大,仿佛在播放一出戏剧。这样的隐私轶事曝得多了,达利越是自述,他的真实生活越是成谜;在后边一点的地方,他甚至不无得意地提到了“伪记忆”的妙处:“伪记忆和真记忆之间的区别,就跟假珠宝和真珠宝的区别一样:假的总是要比真的更真,更绚烂。”
还有一件更奇特的事情:《萨尔瓦多·达利的秘密生活》上市时,封面上就注明,这是一个名叫哈孔·M.谢瓦利耶的人的译本,但其中只字不提作者写作的情况,谁也没见过达利的亲笔书稿——原版本。译本取代了原版,没有人可以核对译本的准确性,得到准确的答案。达利以这种方式,把“初稿”和“定本”的概念都给损毁了,再好奇的人,手里都只有一本书,根本不知如何去研究、去核实。
真是一个比狐狸还狡猾的加泰罗尼亚人。
▍三
达利的狡猾,可以用他的艺术理念来解释——或者说辩护。
谁都看过美丽的西方风景画、静物画、人物画、历史和宗教题材的油画。它们都是前现代和现代的产物,即使到了印象派时期,画面也是给人以美感的。画家们试图确认和树立一些什么,美,崇高,一个人物的身份,或是画家本人的身份,诸如此类。然而,你看达利25岁时的作品《大狂》,他那时就已开始辣手摧花,全盘粉碎前人的基业了。《大狂》是一幅“自画像”无疑,可你在里面看不见达利本人的真实样子,一如他的自传里的诸多回忆,教人着实难辨真假。
没有具体的东西,在一大摊粘糊糊的黄色物体内外,只有一些蚂蚁、一只大蚂蚱、一个女人的侧面以及一个男人的大腿和生殖器是可以看清的,我们几乎辨别不出达利的外貌,不知道哪一根线条可能是他的脸轮。画面里的身份是不稳定的,画家是在杀掉人们对真实和具体的期望,他打观众的脸,而不是感染他们,告诫他们,或荣耀他们。在自传中,作者也故意用含糊、虬曲、夸大其词、自相矛盾的语言,反复表现他的自我:极端自私,喜怒无常,时善时恶,无可捉摸。
他要的就是一个不稳定的身份。他的狡猾就在于,他总是既给出关于他自我的信息,同时又阻止观者形成任何关于这一自我的具体印象;他总能勾引人们的注意,但人看了半天,还是一头雾水。
不能不提到法国精神分析学家雅克·拉康对达利的影响。达利写到过与拉康会面,两人发生争论的事情。拉康认为,画像行为同时包含了认知和疏离两个过程,画布上的图像既是艺术家的一个面向,同时又是独立开来、与艺术家分离的一个实体。它同时是“我”与“非我”。
拉康的观点,撬动了“个体”的根基,个体不再是具体的、稳定的、完整的了。在这个意义上,一个肖像,一个镜(画)中人,实际上脱离了主体,而又向主体投来回望的凝视。《大狂》显示达利很懂拉康这一套,他用这么一些奇特的形象,既勾引观众,又不让他完全看清他的样子,既遮蔽“自我”,又给出一些关于“自我”的暗示。
▍ 四
既然什么都看不清,那么看到“传主真实的一面”一说又从何而来?奥威尔说,他无法确定达利的书里什么是真实,什么虚构,但他闻到了味道:“这是一本发臭的书”,他也领会到了“达利的道德氛围和心理状态”。
达利的成名,差不多是从1930年开始的。最初,他是超现实主义运动的一位主将,这个运动最壮健的两只翅膀,一明一暗,一只叫离经叛道,另一只叫伤风败俗。骂他的人有的是,奥威尔最熟悉英国维多利亚时代以降,经爱德华七世以来越发浓烈的道学风气,他们看见恶心的、按过去的标准根本不宜入画的意象就勃然大怒;与之相反,是那些欢呼欧洲旧道德崩溃,对“附庸风雅之消失”欢欣鼓舞的新大陆的媒体人和商人。达利是在美国大红大紫,走上人生巅峰的,美国的《时代周刊》在1936年让达利上了一次封面,从那时起,看过很多达利“自画像”的人,才算真正开始了解他的模样。
奥威尔对这两类人都十分不齿。他说,达利是个真正有才华的艺术家,“要比绝大多数谴责他的品行、嘲笑他的画作的人强五十倍”,但是,像达利“这样的人能够成功,社会一定出了什么问题”。
我敬佩他的立场。能否做出第三个选择是对人的考验,因为前两个选择,即“支持”或“反对”,总是能够轻松地聚集起智商欠奉、思维能力低弱、行事虚浮、惯于从众的人,而他们永远是社会的大多数。他们总是不能理解,为什么对一件事可以持有,甚至必须持有双重看法。在不懂先锋派艺术的伪善的保守派,和全盘接受达利堕落的灵感、并设法资助他的人之间,奥威尔的第三条道路,是留给那一小撮心足够热、眼足够冷的人的。
他承认达利的天才,但他提醒人们注意,“永远只走一条变邪恶的路,永远只做些骇人伤人的事”:
“在五岁时,将小男孩推下桥,拿鞭子抽打老大夫的脸并且打碎他的眼镜——或至少梦想着这么做。二十年后,拿剪子剜出死驴的眼珠,如此,你总会感觉到自己不同凡人,关键是还能捞到好处!这比犯罪可安全多了。”
奥威尔暗讽达利是在以天才和艺术的名义做不下于犯罪的勾当。不过,与直接诉诸道德讽刺或谴责相反,他对达利的评价是“一个暴露狂和野心家,但不是骗子”——他的画作和自传之中的伪装伎俩,其实是一种自我暴露,他掩藏自己真实的样子,却并不掩盖自己的目的和欲望。
达利的目的是什么?无非名利。奥威尔绝不赞同达利博名的手段,但社会却吃他这一套。时势造就了达利:1930年代既浮华又腐化,“世故之风劲吹,欧洲的每个首都都充斥着贵族和食利者”,,而致力于资助艺术。”达利踩在了风口上,一飞冲天。而在另一篇论阿瑟·库斯勒的文章里,奥威尔更曾写道:“自1930年以后,世界就没有给人们任何保持乐观的理由,放眼望去,除了谎言、仇恨、残忍和无知,没有别的。”达利不把自己包装成彬彬有礼的君子,也不仇恨谁,他只是残忍,好卖弄,缺少起码的道德感,而疯狂追捧达利的人,在奥威尔看来,只是无知。
那么名人,尤其是艺术家,究竟是否应该远离丑闻和恶毒污秽的趣味,洁身自好,给社会做出道德表率?达利这么出众,本该拥有引导社会向善的责任感,可他(在奥威尔看来)反其道而行,还享有所谓“神职人员的特权”:神职人员犯罪,可以不受普通法庭的管束,艺术家恃宠而骄,恣意行事,人们却予以充足的宽容。在这里,奥威尔说出了几句点睛之语:
,如果发现他有在火车车厢里小姑娘的癖好,我们也不能跟他说,你接着干吧,说不定哪天你又写出一部《李尔王》。”
▍五
奥威尔的这篇谈达利的短文,原本要收入1944年的一本文选《周六书》里。但在最后时刻,出版方把文章拿了下来,理由是“淫秽”。
再没有比这更反讽的事了:一篇谈及达利的“淫秽趣味”的文章遭到自我审查,最后被毙,而文章围绕的那部诲淫诲盗的自传却畅销无阻。由此可见,达利当年在西方世界,那真是一呼百应、孤独求败,也正因如此,奥威尔以其勇敢、诚实、三观端正撰文批评,才更值得尊敬。
他还有很多理由可以攻击达利。别的不说,西班牙内战时期,达利带着太太躲去他邦,而奥威尔却远道驰援,参加自己关心的事业,并写下了《向加泰罗尼亚致敬》这部纪实名作。达利的好友,诗人加西亚·洛尔卡惨遭长枪党杀害,达利的亲妹妹安娜·玛丽亚被逮捕、拷打,落下了终生创痛,这些都没能动摇达利保持中立的坚定念头,实在说不过去。他的超现实主义同仁基本都是,同情苏联,崇拜列宁,那时都与他断交了,尤其是该运动的旗手,法国诗人布勒东,直斥达利身上有纳粹主义的味道。——谁能说他讲得不对呢?
▲资料图:达利名画《记忆的永恒》
欧洲战事将起,达利只想躲得远远的,结果选择了法国的波尔多,当入侵法国,他又逃回了西班牙,站在亲佛朗哥的一边。最后,美国人再度向他敞开怀抱,以兼容的天性、“拯救欧洲”的情怀和乐观主义精神,让他安居乐业,名利双收。
但奥威尔克制着,没有挖苦他的胆怯、犬儒、苟且偷生。相反,他既坚定,又略微无奈地告诉我们,要用这样一种眼光来看待达利:艺术可以既对又错,既善又恶,一件作品可以同时闪耀着天才的灵光和无耻之尤的颜色。
“我们应当牢记两个事实,即达利是个优秀的画家,也是个令人厌恶的人。这个事实不能否定或影响另一个事实。我们对一堵墙所提出的要求是,它得立着。如果它立着,就是一堵好墙;至于它立着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另外一个问题。可是,即使是世界上最好的墙,也应该被推倒,如果它所维护的是集中营的话。”
在一个底线之上,把不同的问题分别清楚。像“顾城杀妻”之类隔三差五就要被人翻起的讨论,也是可以拿这段话做尺子来度量的。
▍ 六
称达利为邪恶的天才,绝不过分。有了他之后,人们压抑在内心的很多邪念都盼到了出头之日(并不是绝对的坏事),人们可以无限地想望,从达利那里欣赏到怪诞、诱惑乃至丑恶的行为:它们都被合法化了,以天才的名义。人们用自己的眼球、舌头和钞票鼓励达利这么做。只有奥威尔唱了反调,而且无情地指出了达利争逐名利的真实企图。
虽然同属“西方”,但在欧洲和在美国,达利得到接受的情况是不一样的。1934年后,达利就脱离了巴黎的超现实主义运动大本营,;先锋艺术最慷慨的支持者在美国,但他们抬高达利,主要是出于娱乐的心态——达利愉悦了他们,,,达利式超现实主义成了与卡通片和通俗电影相仿的东西(今天我们看达利不也是这种感觉?)。于是达利虽然成名,他的身份却是一个“大众明星”。
欧洲传统美学观的瓦解,趣味的糜烂,人心的趋恶和非道德倾向,让达利得以自由地把丑恶污秽之物纳入画布,而美国人的娱乐、商业和消费主义,成就了达利本人的偶像化。澳大利亚的艺术史家、批评家罗伯特·休斯,曾将天才艺术家分为两个固定的典型:一是“旧大师”,如拉斐尔、鲁本斯等等,二是“畸人”,如梵·高和高更。他们的公众形象都是真实的,以手画心,一派赤诚,然而,达利的公众形象却是这两类艺术家的扭曲和漫画版,一个“非大师”和“反英雄”。但其实,他也并没有扭曲到位,结果,达利的形象停留在一副故意做出的面孔的层次上,他成了一个被当作偶像供奉的面具,一个Logo,一个纯商品化的东西。
达利式的象征,如融化的钟,蚁群,人的胯、屁股、大腿,着火的长颈鹿,在1930年代初被看作是挑衅固有道德观念的壮举,但当《达利的秘密生活》于1942年出版时,这些离奇怪诞的图像都已为美国人所熟悉、接受并疯狂消费。奥威尔说,“达利是世界所患重病的征象”,这个病就是商业性的偶像崇拜,人们完全不在乎达利画作中呈现的变态心理,不在乎先锋派艺术固有的社会批判意义,相反,一看到他为自己设计的标志性的形象——一对宽而锐利的、疑问重重的眼睛,一抹昆虫触须一样的胡子,会配合嘴巴、脸颊、鼻子、下巴的扭动而盘成一个8字形——他们就激动起来,愿意为他买单。
达利的自我包装,是一个非常好的营销样本,你可以从他的飞黄腾达中学到这种经验:如何将个人形象变成商品和商标,如何精准地出击,每一次都俘获一批有效受众,在他们心里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的经验:你要打出天才、神人、奇人、牛人的名义,也得凭着无耻的精神。虽说,拥有多重身份是达利的梦想,但他很知道这样做的终极目的是赢得公众,他要每个公众都记住他的名字:达利,一个娱乐人物,疯子,艺术家,大众偶像,也是像麦当劳金色拱门那样尽人皆知的商标。
1968年,达利接了一个朗万的代言广告,在电视中,64岁的他向观众展露了他标志性的眼神,那种故意制造出来的不可言传:他真实的自我,已经被这张面具给吸收了。他从罐子里抓出一大把巧克力。忽然,那两根用蜡做的胡子神奇地动了一下,往上翘了起来,他立刻叫出了台词:“I’m mad for Lanvin chocolate!”——我没有醉心于艺术本身,也不再考虑我的变态同世界的污浊之间的对应关系;我疯了,仅仅是因为朗万巧克力。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独立记者,书评人,译者,译有托尼·朱特《责任的重负》、E.萨义德《开端》。 【作者文章推荐】
这里有一群狂热的生娃爱好者
反正将来要移民
我的母亲节手记
更多作者文章,请在对话界面输入“@作者名”调取。
◆◆ ◆ ◆ ◆ ◆◆ ◆ ◆ ◆ ◆◆ ◆ ◆ ◆ ◆ ◆ ◆ ◆ ◆
《大家》在此等你来!
成为大家读者成员,留下你们的声音
当前,《大家》平台互动通道有:微信后台消息、文章评论功能、大家读者信箱及官方微博等,另外还有日渐壮大的读者微信群,该群旨在聚合更多读者朋友,进行线上交流,即时互动,活动参与,福利回馈,等等。
即日起,微信群向读者敞开大门,有愿意加入我们编读交流群的读者,请通过微信后台发送消息“微信号+申请加入大家读者群 ”,我们会尽量及时回复并安排。
※本微信号内容均为腾讯《大家》独家稿件,未经授权转载将追究法律责任,版权合作请联系ipress@fox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