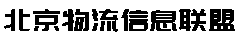
2022-01-05 16:26:33
王秀梅原创作品
隐士(下)
那天晚上,隗醉易在我家中借了宿。我有一间正房,一间厢房,他自己抱了一捆草,在厢房里打了张地铺。江湖中人,随处可睡。我以为他会魂不守舍地跑到青楼里去,但显然他的兴趣点并不仅仅是郑窈窕。不过,我们在喝酒的时候还是谈到了多次郑窈窕。喝酒谈女人,这是人人都擅长的天赋。
怎么说呢,我可以说,我和隗醉易初一见面就相谈甚欢。我躺在藤筐里,隗醉易坐在厢房顶的瓦片上。他登高远望,不停地叙说着对岛的向往。我看着星空。星空神秘莫测。师傅说,每一颗星星都对应着地上的一个人,我不知道像我这样的短人,应该配一颗什么样的星星。
第二天,隗醉易天不亮就走了。我摸了摸厢房地上的草铺,还稍微有点余温。除了这稍纵即逝的余温,再没有什么被留下。两天后我去青楼见了见郑窈窕,她也不知道隗醉易的去向。我们这位新晋朋友无声无息地消失在江湖深处。
日子回归到从前,季节按部就班地向着冬天滑去。我又增加了去码头的次数。渔汛期快要过去了,当寒潮来临,海温下降,渔民们就会把船拖到岸边,让它们好好休整,度过整个冬天。我得赶在冬天来临之前多攒点钱。
直到冬天来临,我们的朋友隗醉易才再次现身。休渔期到了,我不再去码头贩卖海物,开始专心保养我的“大个子”。我买了上好的桐油,给“大个子”一遍遍地粉刷。刷一遍,晾干,再刷。那天我正刷着桐油,我们的朋友隗醉易拎着一只野鸡出现在门口。那湖蓝色的野物肥厚的胸脯上扎着一支短箭,白色的箭羽上滴着几滴暗红的血。
“真是好样的大个子。”隗醉易夸赞着我的独轮车。
“你去哪了?”
“去山里转了转。”隗醉易提一提手里的野鸡。
我在铁锅里烧了热水,拾掇那只长着湖蓝色羽毛的野鸡。隗醉易把它修长的翅翎拔掉,打算用来做箭羽。
那几天,我保养“大个子”,隗醉易制作弓箭。他把野鸡那漂亮的湖蓝色翅翎和尾羽用刀从羽梗那里劈开,粘在箭杆上,再给箭杆装上三棱形的铁箭镞。
“三棱形的箭镞穿透力最强,飞行时阻力小,方向性和准确性好。”隗醉易一边做箭一边向我传授技艺。
“我不懂这些江湖兵器。”我说。师傅教我要低调,我时刻不忘。
“你真不懂?”
“当然。我只是一个贩卖海物的普通人,而且还是个短人,残人。”
“不是每个贩卖海物的普通人都会使剑。”
我停下手里的活儿。隗醉易的话让我心惊。“你在说什么,我听不懂。”我说。
“你瞒得过城里的傻老百姓,却瞒不过我。我是什么人?江湖中人。不过,你不用承认,咱俩过的日子不一样。”
隗醉易继续埋头制作羽箭。我保持沉默,不承认也不否认。师傅教我要诚实。
那个冬天,小城里变得动荡不安。先是几户富商家中被盗,丢失银两财宝无数,接着是县衙午夜遭袭。据说出没于县衙的是一个黑衣蒙面人。不管他打算干什么,幸好尚未得手就被发现。县衙里霎时灯火通明,鸣锣敲鼓,蒙面人脚踩银杏树枝转瞬即逝。
小城里的不安,没有影响我的日常生活。多年来我就一直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漫长的冬季,我靠其它季节积攒下来的银钱,过着拮据却不必担心挨饿的日子。隗醉易也不必担心挨饿,他付给我一些钱,成了我的房客。既然是房客,那么吃饭也在我这里搭伙。我乐于在没有海物可贩卖的冬季成为别人的房东,从而保持一笔稳定的收入。看不出隗醉易靠干什么赚钱,反正他有钱,隔三差五还会拎上几斤牛肉和烧酒回来。他并不像我这样宅在家里,或是顶多到城里去走走,而是神出鬼没不着家。有时他几天不回来睡,有时一睡就是几天几夜,仿佛在什么地方刚刚服过苦役。对他的这种生活方式我也见怪不怪,毕竟他是江湖中人。
有天半夜我上茅房,发现厢房里面多了几个人。房里点着昏暗的烛火,人影映照在窗户纸上,鬼鬼绰绰。第二天傍晚,我问隗醉易,昨晚的人是谁,隗醉易说:
“几个朋友。”
“道上的?”
“文人墨客,谈诗论赋而已。”
我相信了他的话。他跟我这个粗人在一起无法谈诗论赋,我多少觉得有点歉意。
城里的冬天动荡不安。几天后,街上流传着一个新闻,县衙大牢被劫了。两个非常重要的犯人逃脱,狱卒死了十几人。一大清早,县衙里的捕快展开了全城大搜捕,城门封锁,挨家挨户地毯式搜捕可疑人。
谁是可疑人?像隗醉易这样的外乡剑客就是。许多人都知道打外面来了个玉面书生兼江湖中人隗醉易,是城里著名的短人空风华的房客,而且他们把隗醉易的武功传得神乎其神,县衙里的人自然就要把他列为第一可疑人。
面对突如其来的捕快,我像任何一个平头百姓一样胆战心惊。他们腰间挂着代表捕快身份的腰牌,怀里揣着铁尺和绳索,随时随地拿出来惩办有罪和无罪的人。其实我倒不是怕那些铁尺和绳索,以及他们三脚猫的功夫——对付他们,十几个不在我话下。我想了想,大概我害怕的是他们的身份。有些身份是有耀武扬威的震慑力的,捕快作为县衙的鹰犬,那就不必说了。
“捕爷,来收费的吧!冬天可是没有海物可贩卖呀!渔民都不出海了呢!前些天有个胆大妄为的渔民打算出个远洋,没走多远就撞上浮冰,船毁人亡呀!捕爷,行行好,明年开春,明年开春我再交……”这些捕爷,兜里没钱喝酒就跑来找我们要,脑瓜子无穷无尽地编造名目,你随便用敲诈勒索、横征暴敛等词来形容都不为过。
“少来少来!爷几个没空跟你这个短人耍嘴皮子,爷这里可是有比限的!”捕头姓焦,这家伙看来急得不轻。
“焦捕头,您这一‘比’是几天呀?”
“三天!奶奶的,五天过了要是破不了案,爷就等着挨罚吧!”
我立马很配合地带他们去了厢房。我知道里面空无一人。闹腾这么半天,隗醉易即便在厢房里,也早就想办法溜了。他到底跟劫狱有没有关系?我边走边想这个问题。
捕快们很职业化地检查了隗醉易的日常用品:衣服,弓箭,其它一些乱七八糟的无用之物,还有一个香囊,上面绣着花花草草。应该是郑窈窕专门为他做的的女红。草铺冰冷,显然此人早已离去,甚至一夜未归。
我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一样,说:
“我不知道他去了什么地方。或许在青楼里吧。”
“我可告诉你,一旦有了那什么玉面书生的消息,立马跑步到县衙来报!你不是跑得快吗!”
“当然,当然!”我说。捕快的侦破任务是用“比限”来规定时间的,一般都是五天为一“比”,这次缩短为三天,可见逃跑的案犯身份很重。说不定又是郑窈窕她爹那样的反臣。
“奶奶的,这小破地方,还净关押着厉害角色。可苦了咱爷们儿了。”焦捕头骂骂咧咧地带着捕快们呼啦啦全都改道往青楼的方向去了,仿佛是去捉奸。
据说那天,焦捕头一行跑到青楼里的时候,隗醉易还没起床。焦捕头一把掀开帐幔,见隗醉易和郑窈窕睡得正香,隗醉易打着呼噜,嘴角还耷拉着一缕口水。捕快们当然不能错失这次见识郑窈窕的机会,他们掀开郑窈窕的牡丹花被子,终于如愿以偿地看到了她的粉肚兜和其它部分。这多少安慰了比限带给他们的压力。
郑窈窕、老鸨、青楼看大门的,都给隗醉易作了证,证明他从昨儿个天擦黑就腻歪在郑窈窕的房里喝酒作诗,醉得才情大发,作了大概五十首诗,有些还龙飞凤舞地写到了墙上。焦捕头闻了闻隗醉易身上残存的酒味,烦躁地挥了挥手,对捕快们说:
“王八羔子,还看啊?!要不然把你们的狗眼留在这儿,看个够?”
对于青楼里一干人等的证词,我将信将疑。这年头,朝廷昏聩,百姓日子难过,真金白银能让死人变活。我是见识过隗醉易的大手笔的。
夜晚,我躺在藤筐里,跟瓦片上的隗醉易聊天。隗醉易懒洋洋的,一副纵欲过度的样子。
“昨晚跟郑窈窕对了几首诗啊?听说有五十来首。”
“差不多吧。”他一本正经。
“不知道昨夜劫狱的是哪方人马。是单枪匹马,还是几条英雄好汉。你有什么看法?”
“都有可能。”
“不知道他们把案犯藏好了没有。这小城,藏个人吧,说容易也容易,说难也难。”
隗醉易吹起了口哨。“我们聊聊别的,”他说。
“聊什么?”我问。
“造船。”
我本来以为他只是想转移个话题,说说玩的,没想到却是真的。他真想造一条大船,很结实很大,有船桅的那种。为此他专门拉我去码头拜访老渔民。老渔民平生最懂的就是船,他可真是找对了人。我们找了几个人,问来问去,最后确定造船不是科学之举,于是采纳了他们的建议,买了一条船进行改装。
整个漫长的冬季,渔民们不能出海打渔,渔船像一条条搁浅的鱼,躺在海滩上。我们挑选了一条最大最壮实的,隗醉易当场跟船主人完成了交易。接着就是维修和加固了,这也不难办,渔民们恰好都在利用休渔期修补渔船,他们什么工具、材料和招数都有。
我们雇佣的渔民经验丰富,一点一滴地实现着隗醉易的想法。我用到了“我们”这个词——的确,我已不知不觉让隗醉易拉进了修船大业中。反正冬天闲着也是闲着。另外还有个我不愿意承认的原因:我乐于跟隗醉易一起干事,或者闲呆着也行。这个能文能武的家伙,大概就是我父亲曾经希望我成为的那种人。我很遗憾打造了“大个子”的老木匠的离世,否则,我一定把他请来加入到我们的队伍中。
至于隗醉易想用这条规模不小的船干什么,我和他保持了高度的默契,不闻不问。他或许打算开春后自己当鱼老板,以后常年住在这里,靠出海打鱼为生?但很显然,这不符合一个江湖浪子的风格。他必定拿那深思熟虑的家伙另有重用。
漫长的冬天里,小城依然发生着不大不小的事情。,官府派那些不中用的捕快忙活了一个多月,也没查出幕后主使是谁。“比限”因为业务能力的问题而屡屡不能兑现,使得知县焦躁万分。我的朋友隗醉易一直是官府盯梢的嫌疑分子,但他们从来抓不住他半点把柄。别说那些只吃饭干不出好活的烂捕快了,就连我都抓不住隗醉易的把柄。我明明知道厢房里半夜深更时不时地有一些人神秘往来,那里进行着某些神秘的谋划;我也明明知道郑窈窕的闺床有时候被隗醉易当成了挡箭牌;我还知道,隗醉易貌似在厢房里酣睡,但说不定他神不知鬼不觉地已经跑到了十里开外……
他是如此精力超群,简直是个异人。冬天过半的时候,我们的第一艘船顺利完工。它基本实现了隗醉易的想法,是一搜能远洋能载货的好船。我之所以用“第一艘”这样的词,是因为隗醉易的想法并不仅限于这一艘,他还需要好几艘这样的好船。人们都以为,开春后,隗醉易将会成为码头霸主。没办法,谁让他有钱呢。
“你成为码头霸主后,愿不愿意把郑窈窕赎出来?”有一次我试探地问隗醉易。
“我这个人不适合婚配成家。”他说。
“可咱们不能让郑窈窕终生为倡啊!虽说朝廷下了圣旨,咱们也不是想不出办法。比如咱们偷偷找老鸨把郑窈窕赎出来,然后在青楼里面找个容貌相似的姑娘顶包。”
说实话,一想到郑窈窕要终生为倡,我心里就揪得紧。我知道,隗醉易这样的江湖浪子绝不肯在小城里落脚,他办完那件我不知道的大事后就会彻底离开。他确实是个不适合婚配的人,总不能把郑窈窕带在身上飞檐走壁干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吧。这也正是问题所在——隗醉易现在可以用真金白银暂时买得对郑窈窕的专有权,可他一旦离去呢?郑窈窕就要重新沦为一个公有财产,她早晚有一天不给干死也得咬舌自尽。这当然是个最坏的结果,可并非不可能成为现实。一旦成为现实,我就辜负了兵部尚书的嘱托,那我空风华生而为人一顿,还有什么颜面在世上苟活……
我差点就要说出跟兵部尚书之间的那个秘密,关键时候还是把它吞回了肚子里。兹事体大,不容闪失。
冬天过完的时候,隗醉易已经有了他心目中的几艘好船。海冰在温煦的阳光下成片地破碎,哗啦啦地游走或融化,大海重新湛蓝起来。码头上多了一些渔民打扮的人,但瞧着却眼生。隗醉易说,那都是他雇来的打渔人,我问他从哪雇来的,他说,另外一个码头。
这些打渔人个个身体健硕,走起路来无声有力。我是跟着师傅学过剑的,当然懂得从诸多细节中判断一个人会不会武功——很显然,这些人个个身怀绝技,不是普通的打渔人。他们在当地渔民的破海草房里安顿下来,做出一副准备出海打渔的架势。
我预感到,隗醉易要干的那件大事已经到了时辰。在一个看起来跟平时没什么两样的夜晚,我猛然顿悟到了隗醉易的企图。当时我躺在藤筐里遥望星空,隗醉易坐在瓦片上遥望大海。我盯着星空,想象自己是哪一颗星星,师傅又是哪一颗。这时候有一颗原本隐藏得很好的星星突然闪亮起来,星辉夺目。我在星辉中隐约看见了师傅,他没有说话,我却醍醐灌顶。我猛地从藤筐里坐起来,对隗醉易说:
“你要去劫岛!”
我让自己的话吓了一大跳。隗醉易却没害怕,他只是轻描淡写地从瓦片上看了看我,不承认也不否认。
“那些人很重要,是吧?你救出他们来,接着还要干更大的事!”我努力想保持镇定,声音却哆哆嗦嗦的,像忽然回到了三九严寒的冬天。
一切都得到了合理的答案,小城里发生的所有事情,都是更大事情的前奏。会发生什么呢?历史告诉我们,人类的每一次进步,都是新的世界推翻旧的世界……
“你的剑怕是生锈了吧?”隗醉易拔起里一棵刚刚冒出头的嫩草,放在嘴里咀嚼。他怎么可以如此淡定!
我以为自己把剑藏得很好,原来他什么都知道。
“我们打一仗吧。”他说。
都到这份上了,我也无法藏着掖着了。
我们两人在星空下比剑——多么可怜,在我十几年的剑客生涯中,只有那次擂台比武,是我跟真人之间的较量。其它时候,我只能在夜幕掩盖下跟空气较量,或是在脑海里跟想象中的敌人较量。
隗醉易有身高优势,但我的腾跳能力在他之上。而且我攻他的下盘容易得手。我们一来一往斗了几十个回合,最后结果是难分伯仲。
“你是个好剑客,”他说。
“其实我没有一天忘记过练剑。当我推着独轮车贩卖海物的时候,那把剑就在我脑海中舞动。我在意念中已经跟上万个人对决过了。”我很高兴,这些脑海中的练习并没有白费。
“我要留下来保护郑窈窕。”我说。虽然隗醉易始终没承认他要去劫岛的计划,但我认为我们心知肚明。等他救回郑窈窕的父亲,我们再商议下一步的事。下一步……多么令人迷茫!我多希望师傅能从仙岛上驾舟回来一趟,给我指点迷津。
但是,实际上,那年春天又发生了别的事情,不在我们的预料之中,它打破了所有的既定格局。
就在隗醉易紧锣密鼓地做着最后准备的时候,有一天,大海上神秘地驶来了一支船队。那些人是夜黑风高的时候登陆的,上岸之后先劫掠了离海边最近的几户渔民,其中有个曾给隗醉易修过船的,因为不识时务地想护住那点可怜的钱粮,给用刀抹了脖子。
天明之后,那伙人留下洗劫过半的小渔村,不知去向。我和隗醉易当时正在吃早饭,他雇佣的“渔民”呼哧呼哧喘着气跑进来,报告了渔村遭劫的消息。要命的是,隗醉易辛苦打造的海船还丢失了一搜。
“这么说,那伙人是海盗吧?”我揣测道。
“说着叽哩哇啦的鸟语,听不懂。”隗醉易的手下说。
隗醉易咕噜咕噜喝完粥,抹抹嘴巴,站起身,说:
“是海盗无疑。不过,不是咱们大明朝自己的海盗。”
“那是哪儿的?”我问。
“倭国。也就是东瀛、日本。”隗醉易说。他懂的可真多,不愧是江湖中人。
,没想到现在跑咱这儿来了。小倭瓜的贼种!”隗醉易咬着牙根说,腮部一动一动。
“倭瓜是什么意思?”我好奇地追问。
“矮的意思。日本人长得矮,所以叫他们倭人。”
矮小这样的字眼,总是让我十分敏感。怪不得父亲看我不顺眼,原来我长得像遥远的其它国度里的人。
“拉着个脸干什么,说的又不是你,说的是倭贼。”隗醉易看我不高兴,知道说到了我的痛处,“你敢不敢跟倭贼打架?你们个头长得差不多,倭贼也就比你高一点点。”他居然取笑我。
那天我和隗醉易火速赶到了码头。果然,小渔村给整得挺惨,一人被抹了脖子,七八个人挂彩。总的来说还很幸运,隗醉易手下那些人赶跑了倭贼。
“我得要回我的船。”隗醉易说。
“跟谁要去啊?鬼影子都没有一个。”我看了看缄默不言的大海。
“我跟知县要。咱们的赋税不是白交的。”
照我的看法,这事没准能成。朝廷供养的卫所和海防水师应该都不是吃素的吧。
然而我的想法过于乐观了些,隗醉易跑到县衙去交涉了半天,得到的答复是:
“朝廷明令禁止私造二桅以上的海船,你不知道啊?本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就算了,你就别没事找事了。”
“我造船是为了打渔,又不是走私搞贸易。”隗醉易据理力争,却始终得不到下文。
既然当官的不管,隗醉易就打算自己把船夺回来。但倭贼躲到哪里去了,一时半会还查访不到。隗醉易派自己的渔民驾船远远近近搜找了一番,无果。
“等着吧,倭贼还会再来的。”隗醉易说。
我对他的判断将信将疑,但是没几天,果然倭贼又来了。这次他们登陆后先放火烧了几户渔民的海草房,然后趁乱急行军,跑到离县城很近的鸡鸣镇,把那里洗劫一通后,变成了自己的大本营。
为了等倭贼来,隗醉易那些日子一直住在渔村里。倭贼放火后,他率领自己的人跟倭贼打了起来,杀死了几个跑得慢的。等倭贼迅疾撤离后,隗醉易什么都不想,只管跑到码头去找自己丢失的海船。船仍然没找着,倭贼看来进行了严密的分工,一部分占领鸡鸣镇,另一部分驾船撤离了。
官府这才着急起来,组织卫所去打鸡鸣镇。屯田卫所的存在本来就是为了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的,谁知,常年不打仗,加上克扣军饷,强占卫所的田产,军户们偷偷逃亡了大半,剩下的都是老弱病残,根本组织不起一支马上能战的正规军。即便这样,官府还是勉力试了试,结果是,那些丝毫没有战斗力的兵士,只是隔老远朝镇子里放箭,等倭贼一冲出来,他们转身就逃。逃回来的兵士为了尽可能地免责,把倭贼的功夫传得神乎其神,说他们能徒手接住射过去的箭矢。
相比之下,倭贼就有组织得多了。从镇子里逃出一个十五岁的小孩,据他说,倭贼们早上听到公鸡打鸣就准时起床,吃早饭,然后开会布置任务。谁谁去洗劫甲村,谁谁去洗劫乙村。每队都有螺号手,一旦情况不妙就吹海螺,放信号,附近的同伙就飞速赶来救援。傍晚,留在大本营的总螺号手吹响归营的号角,所有人统统归队,清点战利品。
“鸡鸣即起?,才选择了鸡鸣镇作为大本营。”鸡鸣镇家家户户都养着公鸡,清晨时分,啼叫声此起彼伏。其实,我想说点玩笑话让自己放松放松。说实话,听到打外面强行住进来这么一支有组织有规模有纪律的贼寇,我还是挺害怕的。
“我还没听说过能徒手接住箭矢的厉害角色。”隗醉易不相信这个传言。他行走江湖多年,什么样的高手没见过?所以他的判断是有发言权的。
“你难道就不想去看看?反正也不远。说不定倭贼里真有这样的高手,我师傅说过,矮人有天赋。”我说。
“我才不去呢。”隗醉易说:“我要干的事不是这个。这是官府的事。”
“可是……你要是去劫了岛,,简单说,县城被他们给占了,那怎么办?”我觉得我的担忧不是多余的。卫所里的兵士跑了十之八九,没有兵,营盘是空的,还不很简单就让人给占了?
“打仗呗。”他轻描淡写地说:“攻城拔寨。”
“你有兵吗?连卫所里的兵都跑了。”
“这他妈还真是个问题。我手里只有那三五十号人。”他环抱双臂不耐烦地踱步,剑在腰间一抖一抖。
,输送了更多的军备力量补充到鸡鸣镇。,排成长队在田间地头走来走去。间或他们到四邻八乡去劫掠烧杀一番,随处可见某座房子焚烧的烟火。
码头当然也是不安全的。何止是码头,连海上都危机四伏,。海上发生劫掠事件多起,官府只好动用水师进行剿伐。百姓们都知道,咱们这里是有水师的!但他们也同样知道水师根本靠不住,水寨早已名存实亡,战船也都没了。多数被跑掉的水兵驾走了,剩下一艘半艘的,因为没人保养和看护,顺大台风飘走或刮散架了。官府临时组织了一小撮人,,结果可想而知,三下两下就败了。
我恰好看到了那场无法称之为战斗的战斗,所以还是有发言权的。我记得一共有三人生还,连滚带爬地游上岸,其余的都中箭或是中刀,掉到大海里喂鱼了。实事求是地说,那帮倭贼还真称得上骁勇善战,别看个子矮小,但腾跳力强,纷纷跳到我方的船只上,手起刀落,眼都不眨。他们一律手持怪模怪样的弯刀,不知道把刀设计成那样子用意何在。
那是一次近海战斗,怎么说呢,明摆着,让人家打到家门口了。我当时趴在一个鱼摊子后面,瑟瑟发抖。幸好我长得短小,容易藏匿。
我预感到,。于是我找隗醉易交流这事,隗醉易问:
“还能有什么想法?”
“你觉得他们打算一辈子呆在鸡鸣镇,抓些女人睡睡觉生些孩子,在这里安居乐业吗?日本就没有这样的镇子吗?”我循循善诱。
“你不就是想说,他们迟早会攻打县城,然后一路南下吗?”
“我记得你说,。这么发展下去的话,这些贼人迟早要在哪个地方会和。”我仿佛已经看到了那一幕场景。
显然,我们的分析预示着一场可能到来的灾难。“我们是不是应该干点什么?特别是你,你是武功天下第一的江湖高手。”
“你别吹捧我了,我想干的事不是这个。”隗醉易警觉地把思路转移到他的既定方针上去,一副油盐不进的样子。相处这么多日子,我已经多少对他有些了解,他巴不得朝廷倒台。“到处都是昏聩的人,给他们点教训也好。”果然,他这么说。
“可是,你别忘了,还有郑窈窕呢。她还在城里,在呆着呢。,但是人多。”
我一提到郑窈窕,隗醉易就心烦起来。他虽是武林高手,但同时也是擅长吟诗弄赋的才子,才子都是多情的。
“英雄总是为红颜所累。”他说,“不过你倒提醒了我,做人要及时行乐。”
于是隗醉易就抓紧时间行乐,基本上每晚都去青楼会会郑窈窕。有一天他半夜回来,睡不着,在厢房里折腾半天,跑到我房里,说要跟我聊聊。我说,聊吧,聊一天是一天。
“郑窈窕也问了相同的问题。”他说。
“什么问题?”我并非明知故问,而是不敢相信一个会琢磨国事。
“她问我,。”隗醉易又说:“她不知道我要去干一件更重要的事。”他仿佛是在为自己辩解。
我直觉,郑窈窕即便知道了隗醉易要去劫岛,去救她父亲及其他在隗醉易眼里看来非救不可的重要人物,。虽然郑窈窕是一个,但她并不是一个通俗意义上的,她是兵部尚书的女儿,通晓琴棋书画、历史当下。
说实话,我也很迷茫,不知道应该干点什么。码头那边危机重重,许多鱼贩子都识时务地歇菜不干了,只有我还一如既往地往返于码头和县城之间。我倒不是非要去贩卖海物不可,只是,那是我这一生唯一能干的事。我的“大个子”也是生来如此,它一定也不喜欢闲着。所以,师傅在上,只要有一个渔民还在出海,我就要贩卖海物。
车轮行走,辐条此起彼伏,周而复始。这就是我和“大个子”的宿命。虽然我总是挑小路走,近码头时先找地方躲藏起来,观察好形势再去跟鱼贩子交易,但有一天,。
我是在返回途中碰到那帮倭贼的。他们不知从什么地方突然冒了出来,共有五人,霎时就把我和“大个子”围在中间。说出来真是丢师傅的脸,我当时吓得差点尿了裤子。,根本不必大动干戈,索性调笑一番再说。他们揪扯我的胡子,叽哩哇啦地乱说一通,我猜大概意思是说我不是个小孩,而是个大人。个子像六七岁的小孩,脸上却长着浓密的胡茬,我这副形象让他们笑得快要岔了气。
他们不停地推搡我,逗弄我,在我身边转来转去。他们很爱转圈。我很紧张地观察着他们身上的兵器,发现他们有两人手拿弯刀,两人手拿长枪,另外一人拿着一把弓矢。这些兵器看起来都挺精巧的,倒是跟我的小剑有点般配。除了这些兵器,这五人全体光着脚丫子,上身只穿一件单衣,下身更甚,奇怪地只有一片布兜,仅能遮住裆部而已。他们的头发也不像我们留得那么长,而是短短的还剃成半月形。先不说审美差异,单说说咱们老祖宗留下的古训: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
过后我百思不得其解,在生死存亡之际,我竟然还抽空想了想古训。由此可见,人在面临重大危险时,思维是很活跃的。我想到古训时,还强烈地想了我的父亲。虽然他待我凉薄,但老天知道,那会儿,我想他想得要命。我甚至想,今天我空风华就是死了,也不丢失一根头发,那是我爹娘给的。
我本来想,,只要他们放过我,我就推着“大个子”赶紧走人。师傅说了,做人要低调。但是这帮人逗弄我也就罢了,大概觉得无聊了,转而去逗弄“大个子”。他们可能见过侏儒——我猜日本也会有侏儒——却没见过侏儒的独轮车,因此倍感好奇,东摸摸,西踹踹,。听隗醉易说,,想必从没推过独轮车,这可把“大个子”害惨了,不说也罢。
这可是我不能容忍之事,我可以受辱,我的“大个子”不能受辱。总之,等到实在忍无可忍的时候,我终于爆发了。我用快得不能再快的速度,从“大个子”身下抽出小剑,唰唰唰连着三剑,。
连着干倒三人,是我最快的速度了。还剩下两个,情况就不那么乐观了,因为他们有了喘息的时机。说真的,从头至尾我都怕得要命,我想,我大概根本就不是当剑客的命,剑客的字典里应该没有害怕两个字。
,一人持刀,一人持弓矢,窝着身子跟我对峙。持弓矢那人觉得手里的武器不利于近身肉搏,频频打算去捡他死去的朋友的剑或刀,却被我死死盯住。我们对峙了良久。师傅教我要沉住气,,两人交换了一下眼神,持弓矢那人猛然朝我逼近,意欲牵制我,以便让同伙下手。我瞬间就看出了他们的意图,说真的,我根本没想到自己会有这么迅速的临阵反应能力。他们大概都认为侏儒善于贴近地面战斗,我偏出乎他们的预料。我忽地腾跳起来,脚尖在旁边的一棵老槐树上用力一点,借力,改变方向,。
说真的,当我拔出小剑时,整个人都处在极度的惊讶之中——难以想象,刚才那一式的方向、速度、力量怎么会那么恰到好处,简直是鬼斧神工,多一丁点嫌多,少一丁点嫌少。
我不敢相信自己的功夫到了这样出神入化的程度,那就惟有认为这是巧合了。或者,是师傅冥冥中在助了我一臂之力。
,我那时候已经杀红了眼,而且技术上处于巅峰状态,怎么说呢,想让自己出个笨招都出不了。我是怎么杀了最后一个倭贼的?很简单,我从倒数第二个死掉的倭贼头顶上拔出剑,落地之前,顺便用它抹了最后一个倭贼的脖子。
。这是我人生中最重大的事件之一。
“我没看错你。”隗醉易说,“这下我就放心了,郑窈窕就交给你来保护。我回来时,你要把她好好地交给我。”
这么说,隗醉易是铁下心要去劫岛了。我知道,像他们这种江湖中人,都是固执的理想主义者,或许他们必须这样活着,否则,人生了无意义。
隗醉易定下了出海的日子,是个月黑风高的晚上。他提前找人夜观天象,得知那几天无风无浪。作为他的房东兼好友,我必须去码头送他一程。此一去,不知今生还能不能再相见。
他带领着三十几号人,分乘三艘海船,兵器、粮水都准备齐全。在码头上,我给隗醉易倒了一碗酒,说:
“隗兄,就此别过。”
隗醉易一口喝干了酒,把碗还给我,说:
“拿回去,还能用。郑窈窕交给你了。要是我没回来,你接管。”
“我此生不。”我说。
“你是天底下头号大傻瓜。不解风情。”
“我又不写诗。”
“我知道,你自卑。”
他此去凶险,我也懒得跟他在嘴皮子上一较高下,我们再次抱拳准备别过。谁知,就在这关头,上次从鸡鸣镇逃出来的那孩子气喘吁吁地跑来,大呼小叫:
“他们在攻城!”
当啷一声,我手里的碗落地摔碎了。这真让人心疼。
看来,我的预感没错,,然后长驱直入,向西,向南。我看了一眼隗醉易,又看了一眼。隗醉易说:
“你老看我干什么?我只能说,你猜对了。你是个杰出的军事家,比那些吃皇粮不拉屎的家伙强。”
“情况如何?”我问那气喘吁吁的小孩。小孩比比划划地说:
“城里的守卫朝下射箭,,然后再搭弓反射回去。守卫都吓坏了。”
还真有这事!我又看了一眼隗醉易,我赌他会跟我进城。他在做激烈的思想斗争,好半天,我都快沉不住气了,在心里央告了好几次,让师傅给我点力量,让我沉住气。终于,他气急败坏地说:
“空手接箭?看看去。”回头又朝三艘海船吆喝:“愣着干什么?下船啊!”
船上的人面面相觑,接着呼隆隆都下了水,朝岸上跑,水花四溅。
那是一场很耻辱的战斗,我们跑到城下的时候,,。因为平素缺乏操练,素质太差,,手脚哆嗦,箭好歹算是射出来了,但软绵绵的没什么力气。,让那家伙一把就拽了下来,然后,那家伙好像挠痒痒似的拍了拍屁股,朝城墙放了个响屁。
射箭素质低,放鸟铳也不是对手。我们老远就看到城墙上守卫手里端着鸟铳,但枪声却稀稀拉拉。隗醉易骂道:
“妈的!不是铅子掉地上了,就是火绳没接好。都是些吃屎的。”
这可真不像风流才子说的话。
这还不算,忽然城墙上有人大叫道:
“西门攻破了!”
隗醉易更生气了,带头就往西门跑,边跑边骂:
“倭贼还挺懂战略战术,各个击破呀!”
等我们跑到西门,看到果然城门被破,里面的官兵都虚张声势地冲了出来,其中还夹杂着城里的百姓。两支队伍短兵相接,明显可看出技术上的悬殊。,上下翻飞,白光一片,霍霍生风。而且他们上下左右地腾挪跳跃,像猴子似的,让人难以锁定。我方兵士本来战斗力就弱,见敌人如此骁勇善战,气势上首先就败了,多数人虚晃几下就逃回城里去了。
形势很危急,,麻烦就大了。,并不是像我们一样,散兵游勇,乱七八糟。城墙根下有个穿红衣服的头儿,骑在一匹马上,手里握着一柄扇子——不同于诸葛亮的羽扇,但功用相同——很有规划地挥来舞去,阵形接着就变了。隗醉易嗷地大叫一声:
“郑窈窕还在城里呢!”
他的人马跟着他就往前跑。,穿红衣服的头儿立即挥舞扇子,变换阵形。隗醉易说:
“嘿!摆阵呢!我管你什么阵,弟兄们,开火,抄刀,死命地追!”
凌晨时分,战斗结束了。。我们进城以后,隗醉易先跑到青楼去会郑窈窕。我想,他们应该好好吟吟诗作作赋睡睡觉,隗醉易今天功不可没。
我一个人落寞地回家,跟随着我的只有“大个子”。在战斗的过程中,我一直推着“大个子”,它帮我挡了几支箭。,四肢却孔武有力,其中有一支箭居然射进了上好的阴沉木里。我把它小心翼翼地拔了出来,但木头上还是留下了一个洞,像伤疤。
这就是那年春夏发生的事情:,打乱了隗醉易的既定规划。他没有一天不嚷嚷,要干他该干的事,。嚷嚷归嚷嚷,他却一直留在这里,。他扩大了队伍,从外地带回了上百人,又在本地招募了一些渔民。江湖中人总是很神秘的,有许多办法。官府兵力不行,只好巴结隗醉易,他们做了一些交易,使这些民兵有了粮饷和装备。装备不仅包括盔甲,还有鸟铳。
这么一来,隗醉易就更走不了了。他痛骂官府是群狡猾的骗子。,我压根不想留在这里。”他说。但直到他战死,。
是的,隗醉易最终战死了。那是第二年的事情。他用十五战十五捷的骄傲战绩,把自己送进了坟墓。,可不是那么容易被消灭的,还需要时日……他从没有一刻忘记过劫岛的计划,但每次想起,就被眼前的事所干扰。“唉,还是先干掉倭贼再说。总不能由着他们来抢咱们的地盘。大明该灭,但得由我们自己人来灭。岛就在那里摆着,一时半会儿消失不了。”
关于隗醉易的死,没有什么好说的。像这种江湖中人,武艺越高强,死越是瞬息之间的事。就连我这个低调之人,也只是侥幸没死而已。我丢了一只眼睛。日本人四肢太发达了,那支箭像闪电一样刺进了我的左眼。
我有生之年遇到过许多次生死攸关的时刻,每到那个时刻,我都强烈地想念我的父亲。我拼力保全自己的身体,因为古训教导我,那是在守孝。那支箭射进我左眼以后,我想起三国时的夏侯敦,便决定效法他。我拽住那支箭,把它小心翼翼地拔了出来。还好,如我所愿,左眼球也顺利地给拔出来了。
然后,我把我的左眼球吃了下去。
从此,我这个短人就更残废了。为了美观一些,我像别人一样,找了块黑布,把空空的眼洞挡住了。但他们不知道,我那只眼并没废,我仍能看得见。因为我没把它丢掉,而是吃进了肚子里。它在我肚子里炯炯地亮着,比在眼眶里呆着的那只都明亮。
一个夜里,我躲在青楼后门口。没有月光,小巷子里暗黑。老鸨打开门,朝我怀里塞了个包裹,说:
“郑窈窕没了。出血太多了。孩子总算还活着。赶紧走吧,再别来了。唉哟,我这干的可是杀头的事儿,她们是有圣旨的。”
我把包裹放进藤筐里,推起“大个子”一路疾行。
再后来的事儿就没什么可说的了。日子过着,一切都按部就班地成为了历史。我继续往返于码头和县城之间,干着我的鱼贩子买卖。只不过,我贩卖的海物比以前减半了,因为要腾出一只筐来给我的儿子。那包裹里的小孩也按部就班地成长着,小胖手里抓着海物,尖声细气地叫卖:
海蛎!花蛤!扇贝!海虹!还有鱼!
海蛎!花蛤!扇贝!海虹!还有鱼!
我再也不寂寞了。我给儿子讲很多人和事,比如我的师傅菇蒲散人。我猜他大概炼成了仙丹,羽化成仙了。
城里的许多人都猜测着那孩子的来历,有些人猜得很对。
孩子越长越大,开始问我一个问题:
“我娘真的是吗?”
我能怎么回答呢?我只好说:
“你爹是江湖高手。”
《长江文艺》2016年第7期
王秀梅
著有《大雪》《一九三八年的铁》《去槐花洲》《浮世筑》《初朵的秋天》等作品二十余部,部分被译介为希腊文、英文等国文字。曾获多种奖项,作品多次被转载和入选各种选本。中国作协会员,烟台市作协主席。
王秀梅的槐花洲
所有文章均为原创
相关推荐
友情链接
Copyright © 2023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北京物流信息联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