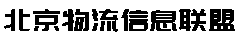△让·莱昂·热罗姆,法庭上的芙丽涅
约翰•伯格,真的老了,如今已90高龄。他的系列作品,断货许久后,终于出了新版。他是当代最有影响力的作家、艺术评论家、公共知识分子之一,在艺术评论方面,他主创的BBC电视节目《观看之道》影响了西方一整个世代的观看方式,同名图书也成为艺术史必读经典,在虚构写作方面,他的小说《G》获得了堪比诺贝尔文学奖的布克奖。
可能还有不少读者朋友不了解他,且引用一段陈丹青的评语:“他不倦的窥探并非仅仅指向摄影与绘画,而是‘观看’的诡谲......阅读伯格,会随时触动读者内心极为相似的诧异与经验,并使我们的同情心提升为良知。”借大家熟悉的人物去引介另一位,有点尴尬,老套的手法了,实在也是说得好。
最初想做约翰•伯格的微信时,还请责编尝试摘录几本作品的精彩观点或语录,责编也马上做了,比如:
“在人类的属性中,永不缺席的脆弱,最为珍贵。”“表演必须有风格。必须在一个晚上连续征服观众超过两次。为了做到这点,那些层出不穷、接连不断的插科打诨,必须导向某个更神秘的东西,必须引出那个诡诈又不敬的命题:生命本身就是一场单人脱口秀。”(《我们在此相遇》)
“那些我们不爱的人,与我们有着太多的共同之处,以至于我们无法爱他们。激情只为另一个人而生。在激情里没有情谊。但是激情能够赋予爱人双方相同的自由。这个自由的共同经验——本身如星辰般的、寒冷的自由——或许能在他们之间发出无以伦比的柔情。”
“当一个健康的人选择时,终究是因为没有人理解他。他去世之后,误解通常会继续,因为活着的人总是为着自己的便宜,诠释、利用他的故事。如此一来,对误解的强烈抗议根本没有人去理会。”(《讲故事的人》)
“如果一位作家的动力不是来自对最苛刻的语言之准确性的渴望,那么,他就无法接触到事件的真正歧义。”
“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性别,自己的年龄,这和人口统计学没有什么关系。罗马是女性。熬德萨也是。伦敦是一个少年,一个顽童,而且,关于这一点,从狄更斯的时代开始就没什么变化。 巴黎呢,我相信,是一名男子,正当二十多岁的年纪,却爱上了一位年长的妇人。”(《约定》)
......
后来,转念一想,这样呈现,是否有把一个渊博立体的伯格简单化、粗暴化,乃至自己鄙视的鸡汤化的嫌疑?
还是摘录一篇有关“情色”的文章吧。如何看待艺术中的“情色”,或许最能直接体现一个艺术评论家的水准。
✦✦✦
性 敏 感 区
文 | 约翰·伯格
主题支配着毕加索画家生涯的最后阶段。看着这些晚期作品,我再次想起威廉·巴特勒·叶芝(W. B. Yeats)晚年所写的诗句:
你以为这很可怕?色欲和怒火
竟向我这耄耋老人殷勤献媚;
我年轻时它们并不如此烦扰;
世间还有何物平添我的诗兴?
然而,为什么这样一种困扰如此适宜于绘画媒介?为什么绘画能够使它如此意味深长?
![]()
△创作中的晚年毕加索,1958年夏。大卫·道格拉斯·邓肯拍摄。
试图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稍稍厘清一下基础。弗洛伊德式的分析在此没有太大帮助,不管它在别的场合多么管用,因为它关注的主要是象征意义和潜意识。而我提出的问题却是直接关于身体,并且显然属于意识领域。
我想,就算是色情哲学家——例如著名的巴塔耶(Bataille)——也起不了什么作用,这同样是因为(不过却是以不同的方式),在这一问题上,他们容易过分注重文学和心理学因素。我们必须相当简洁地考虑一下颜料和身体样貌。
最早绘制的图像展现的是动物的身体。从那以后,世界上大多数绘画表现的都是这类或那类身体。这并非为了贬抑风景或其他后起的题材,也不是为了建立一种等级体系。但是,如果我们记得,绘画之首要和基本目的,是为了唤起那不在场的事物的在场,那么,一般而言绘画召唤的是身体这一点也就不足为奇了。它们的在场正好合乎我们在集体荒居和个人独处时的所需,我们从中得到安慰、强化、鼓舞或激励。绘画陪伴我们的眼睛。而这陪伴通常包含身体。
![]()
△西班牙阿尔塔米拉野牛壁画,距今约有1万-3万年。
现在我们考虑一下其他艺术——尽管冒着过度简化的巨大危险。叙事小说涉及行动:它们在时间上有一个开始和结束。诗歌表达心境、伤者、死者——所有那些在我们的主体间际领域有其存在的事物。音乐是关于隐藏在给定事物背后的东西:无言的、无形的、无拘无束的。戏剧重演往昔时光。绘画是关于物理的、可触的、眼前的事物(抽象艺术面临的无法逾越的难题,即是克服此点)。最接近绘画的艺术是舞蹈。两者都源于身体,召唤身体,在语词的最初意义上,都属于肉身。一个重要的区别在于,舞蹈就像故事和戏剧,有一个开始和一个结束,因此存在于时间之中;而绘画则是瞬时的。(雕塑在类别上自成一格,因为它显然比绘画更加静态,并且往往缺乏色彩,一般没有框架,因之较少私密性,不过这个问题需要另行撰文阐述。)
于是,绘画提供了可触的、瞬时的、不偏不倚的、连贯的、肉体的在场。它是众多艺术之中最直接可感的一门艺术。从身体到身体。其中之一是观众的身体。但这并不是说,一切绘画的目的都是感官;因为许多绘画的主旨是禁欲。很多世纪以来,从感官获得的信息,随着意识形态的不同而变化不定。同样,性的角色也在变化。
![]()
△丁托列托 维纳斯,华尔康及战神
![]()
△马奈 奥林匹亚
例如,绘画可以把妇女呈现为一个被动的性对象,一个主动的性伴侣,也可以呈现为一个嗷嗷待哺的人,呈现为一个女神,呈现为一个为人所爱的凡人。然而,不管我们怎样运用绘画,这种运用都始于一种深刻的感官刺激,接着,这种刺激四散传播开来。想想一个画中的颅骨、一支画中的百合、一张地毯、一块红窗帘、一具尸体——在所有这些例子中,不管结局如何,开端(如果那画富有生气的话)都是一个感官的冲击。
一个人言及“感官”之时——这里涉及人的身体和人的想象力——同时也就是在言说着“性”。正是在这里,绘画实践开始变得更为神秘。
在许多动物和昆虫的性生活中,视觉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色彩、外形和视觉姿态警示和吸引着异性。对于人类来说,视觉的作用尤为重要,因为信号不仅表达了本能反应,还表达了想象。(视觉在性行为中所起的作用,对男人比对女人更加重要,但是这个差别很难衡量,因为男性至上主义传统在现代的图像制作中已经根深蒂固。)
![]()
△佚名 浴中加布莉埃尔与她的一位姐妹
、、耻骨和肚子是性欲的天然视觉焦点,而且它们的肤色也增强了它们的吸引力。假使人们很少直截了当地说出这一事实——假使人们把这一事实遗弃在公共围墙上自发涂鸦的领域之中——这应归功于清教主义道德说教的重负。事实上,我们都是这样长大成人的。在其他时代的其他文化中,人们却曾利用化妆和美容的方法,刻意突出这些部位的吸引力和向心性。化妆可以为身体的自然色泽增色不少。
假使绘画是适当的身体艺术,假使,为了履行繁衍生息的基本功能,身体使用了视觉信号和性诱刺激,那么,我们就会开始了解为何绘画从不远离于性感部位。
![]()
△丁托列托 裸胸的妇女
丁托列托画了一幅油画,《裸胸的妇女》(Woman with Bare Breasts),现藏于普拉多。画中女子敞开了她的胸脯,因此我们可以看见她的,这幅画同时也代表了绘画自身的天资和禀赋。在最简单的层面,当它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及其光晕时,绘画(不管多么高明)只是在模仿自然(不管多么巧妙)。这是用于同一目的的两类非常不同的“肤色”。
然而,正如只是身体的一部分,的敞露也只是画面的一部分。这幅油画还描绘了女子冷淡的表情,拒人千里之外的双手姿势,她半透明的服装,她的珍珠饰品,她的发型,她披散在脖子上的头发,她身后肉色的墙壁或帷幕,以及,所在皆是的为威尼斯人所深爱的绿色和粉红之间的游戏。凭着所有这些要素,画中女子利用真人的可见手段引诱着我们。在这同一的视觉卖俏中,两者乃是同谋。
丁托列托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他父亲是一个布料染工。儿子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远离这个行业,进入了艺术领域,却仍是一个“染工”,身体、皮肤、四肢的“染工”,像所有画家一样。
![]()
△乔尔乔内 一个老妇人
让我们想象一下,如果把丁托列托这幅画和乔尔乔内作于半个世纪前的绘画《一个老妇人》(An Old Woman)放在一起,会是怎样一番情景。这两幅画都表明了,存在于颜料和肉体之间的密切而独特的关系,并不必定意味着性的刺激。相反,乔尔乔内那幅画的主题正是这种挑逗力量的丧失。
也许没有任何语言能像此画一样记录一位年老妇人的肉体的悲哀,她的右手手势与丁托列托所画的女人是如此相像,可是又是如此不同。为什么呢?因为颜料已经成为那具肉体?这几乎是真的,但还不完全是。毋宁说,是因为颜料已经成为那具肉体的传达,它的哀悼。
![]()
△提香 万事皆空
最后,我想起提香的《万事皆空》(Vanity of the World),藏于慕尼黑。画中女子放弃了她的所有珠宝(除了结婚戒指)和所有装饰。这些弃而不用的“矫饰”,在她手中拿着的黑色镜子中反映出来。然而,即使在这里,在这个最不恰当的背景下,她的画中的头部和肩膀仍然为愿望而高呼。而颜料就是这呼喊。
这就是颜料和肉体之间的古老契约。这个契约使得描绘圣母和圣婴的伟大绘画呈现出深刻的感官安全和愉悦,正如它也把它们的悲痛的全部重担赋予了伟大的虔敬——肉体将会复活,这个无望的欲望的可怕重负。绘画属于身体。
![]()
△马奈 草地上的午餐
颜色的材料具有一种性的冲力(sexual charge)。马奈创作《草地上的午餐》(Le Dejeuner sur I’Herbe)(这是毕加索在他的最后阶段临摹过很多次的一幅画)之时,颜料公然的苍白,不仅模仿了,而且自身也成为了草地上的女人那公然的一丝不挂。绘画所展示的就是被展示的身体。
绘画和肉身欲望之间的密切关系(相互作用)——人们必须从教会和博物馆、学院和法庭的束缚下把它解放出来——和油画颜料的特殊的拟态纹理几乎无关,这一点我已在《观看之道》(Ways of Seeing)一书中讨论过。这种关系始于绘画行动,而不是绘画媒介。这种相互作用同时也存在于壁画或水彩之中。画中身体的幻觉主义的可触摸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们的视觉信号,这种视觉信号和真实身体的视觉信号之间有着如此令人震惊的串谋。
也许现在我们可以略较先前更好地理解毕加索在他生命的最后二十年所做的事情,他是被动的,而且——正如人们可以预料的——从未有人这么做过。
![]() △老年毕加索与妻子杰奎琳在在画作“Bañistas en La Garoupe ”前跳舞,1957年。大卫·道格拉斯·邓肯拍摄。
△老年毕加索与妻子杰奎琳在在画作“Bañistas en La Garoupe ”前跳舞,1957年。大卫·道格拉斯·邓肯拍摄。
这时他已经老了,可是还像以前那么骄傲,还像他一向所是的那么好色,只是如今他面对的是自己相对而言力不从心的荒谬情形。世上最古老的玩笑之一,成了他的痛苦和他的困扰——同时也挑战着他的无比骄傲。
与此同时,他生活在一种异乎寻常的、与世隔绝的状态之中——这种孤立,我已在书中指出,并非完全出自他自己的选择,而是因为他的巨大声望。这一隔绝状态的孤寂无法纾缓他的困扰;相反,它越来越把他推离开任何其他的兴趣或关注。他注定处于一种无路可逃的忠贞之中,一种狂热之中,这一状态采取了独白的形式。独白是一种言说,面对的是绘画实践,以及所有他所仰慕,或者热爱与妒忌的已故的昔时画家。此一独白关乎。作品不同,独白的意境也各有千秋,可是主题不变。
![]()
△伦勃朗 自画像,1669年
伦勃朗的晚期绘画非常出名——尤其是那些自画像,因为它们质疑了艺术家以前曾经做过或者画过的一切。一切都在另一种光照下得到审视。和毕加索几乎活得一样长的提香,当他临近生命终点的时候,在威尼斯创作了《马斯亚斯之剥皮》(The Flaying of Marsyas)和《圣母怜子图》(The Pieta):这是两件非同寻常的绝笔之作,在这两件作品中,颜料就像肉体一样变得冰冷。
就伦勃朗和提香而言,他们两人的晚期作品和早期作品之间的对比非常明显。不过,仍然存在一种连续性,可是这种连续性的基础很难简单地加以界定。这是图像语言、文化参照(cultural reference)、宗教信仰和艺术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的连续性。这种连续性缓解并调和了——在一定程度上——这些年老画家的绝望之情;他们感受到的孤寂变成了一种悲伤的智慧或者一种乞求。
![]()
△提香 圣母怜子图
或许是因为不存在这种连续性(原因很多),因此,这种情况并未发生在毕加索身上。在艺术中,他孤身一人完成了许多毁灭性的工作。但这不是因为他是一个反传统主义者,也不是因为他不能忍受过去,而是因为他憎恨关于教养阶层的因袭的半真(half-truths)观念。他以真理的名义大肆破坏。可是他所破坏的东西没有来得及在他死前重新纳入传统。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他临摹了一些昔日的大师,例如委拉斯开兹、普桑或德拉克洛瓦,这些临摹是为了试图寻找伙伴,为了重建一种断裂的连续性。它们允许他加入它们。但是它们无法加入他。
因此,他孤身一人——老人向来如此。但他是全然孤独的,因为他已从当代世界中被切下,成了一个历史人物,成了连续的图像传统下的一位画家。再也没有什么对他言说,再也没有什么束缚着他,于是他的困扰成了一阵狂乱:智慧的反面。
![]()
△毕加索 阿尔及尔的女人
一位老人,狂乱地迷恋着他再也无法制造的美感。一场闹剧。一阵狂暴。这一狂乱如何表达自身?(如果他不能每日画画,或许早已疯掉或死掉了——他需要画家的姿态,以此证明他仍然是一个活人。)狂乱表达自身的方式是直接回到颜料和肉体,以及它们共有的符号之间的神秘联系。这是颜料作为一个无限的性敏感区的狂乱。然而这共有的符号,如今并不指示彼此的欲望,却显示了性的机能。粗糙。带着怒气。带着亵渎。这是诅咒的绘画,诅咒自己的力量,诅咒自己的母亲。这是冒犯那曾被誉为圣洁之物的绘画。从前没有人能想到,绘画怎么可能在起源上是下流的,这可不同于图解的下流。而毕加索发现了它是可能的。
![]()
△毕加索 画家和模特儿
![]()
△毕加索 草地上的午餐变奏
怎么评价这些晚期作品?有人妄称它们是毕加索艺术的巅峰之作,他们就像围绕在他身边的圣徒传记作者一贯所是的那样愚不可及。有人不屑一顾,把这些作品视为一个老人没完没了的喋喋不休,他们完全不懂得情爱或人间苦难。
众所周知,西班牙人自傲于他们能够起誓的方式。他们欣赏他们誓言的别出心裁,而且他们知道宣誓可以成为尊严的一个标志,甚至是一个证据。
在毕加索画出这些油画之前,没有人曾在画中宣誓。
![]()
-END-
![]()